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母亲聊天。前几天她和几位小区邻居阿姨们一起去笔架山公园赏花游玩,几人中她年龄最大,但就她没带那种专门用来装饰拍照的假发。我说:「妈,你这发型发挺好看。」她最近做了一个体检,医生说她心脏供血不足,如果感觉胸闷疼痛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医生给她开了一种小药片,一小袋共五片,叮嘱她在危急的时候吃下一颗,然后紧急前往医院。
儿子:「还是得再去检查看看。」
母亲: 「就这样吧,不太想治疗。」
儿子:「那我们还是去医院做个系统点的检查,查个清楚,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即便不想治疗,我们心里也得有个明白,是吧?」
母亲笑着说:「死也得死个明明白白是吧。」
这几年我和母亲谈论疾病和死亡,很少有沉重与悲伤。
母亲比我通透,她之前跟我聊过一次「身后事」的安排。她的丧事想在深圳安安静静地办,不要通知江苏老家的亲友们大老远赶到深圳来,不想让他们那么麻烦,她自己也不想那么吵闹,她说:「安静点好。」如果可以的话,申请一下将骨灰撒大海或者随便埋在山脚下的树旁就行,要那个小盒子没有意义。
她说:「等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你回去跟家里人,你舅、姨们通报一声就行了,就算是有一个交代了。」
母亲说:「不要葬回老家村上,不要跟你爸葬一起。」她对这个男人的恨,时间无法抹平。
回家过年期间跟父亲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如果你妈不葬回来,那她就成孤魂野鬼了。」母亲对父亲的话甚是鄙夷,她不信村上说的鬼神,她不屑于村上的那一套吹吹打打。她信基督,她相信耶和华不会抛弃她。
她只是一位普通女性,但在面对生死问题上,她有点宗教家或哲学家的影子。已故学者李泽厚先生曾给自己写了一段话:「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
母亲对死亡的通透,一是因为年岁带来的礼物,另外是因为她曾多次直面过死神的捉弄。
11年前,母亲在湖南做过三次开腹手术,术后胃部有一个切口一直未愈合,需要用一根管子把漏到腹腔的胃液倒流到体外,要不然便会腐蚀内脏器官,她已因此有过多次生命危险。在医院病床上待了一年多时间,一年多一直靠静脉输入营养液维持生命,从未吃过一口东西。后来她身上带着倒流管回家调养,也只能喝点稀薄的汤汁,床头的负压机得一直替她吸收着体内的液体。食物对于她来说,就是致命的东西。
在家里又躺了一年多时间,有一天,她说:「想明白了,不想再带着管子等死了」,县城医院不敢给她拔管子,她自己在家把那根深深插在身体里的管子拔了出来,看着管壁上积累的那些污渍,她扔掉了它们,就像是扔掉了过去两年的自己。当然,也可能就此告别今世的自己。她走上街头,吃了一块苏北烙煎饼,那块煎饼是她送给自己依然活着的奖赏,也是她可能奔赴死亡的仪式。她面对死亡时的勇敢有点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希腊人判处死刑,饮鸩而亡。那根管子就是命运对她的审判,那块煎饼就是她的毒药。
母亲说:「两年多没正经吃过东西了,那块煎饼太香了。」不知是上帝那会还不太想收留她,还是阎王爷刚好在她吃煎饼的时候打了个盹,她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后来,曾在湖南救治过她的一位老教授把她的治疗过程写入了教材。再后来,母亲跟我来了遥远的深圳,病魔也远离了她瘦弱的身躯。
生命渺小如草,也坚硬似钢。
周末早晨,本想睡个懒觉,睡前忘记把六点多的手机闹铃给关掉,闹铃准时响起,睡意退去精神尚佳,起床阅读。母亲进门见我坐在灯下,问:「周末起这么早吗?」我故作神气地说:「勤劳的人还分周日和周一吗?」母亲笑了笑,去厨房给我和孩子们准备早餐,这是她最大的心愿——每一天都能给孩子们做点吃的,不分傍晚与清晨。
我放下书,坐在桌旁听着厨房发出的声响,那切菜板上我永远学不会的时快时慢却节奏一致的声音,那碗碟碰撞的清脆声、配料入锅的滋啦声、水龙头时缓时急的哗啦声,更换垃圾袋的沙沙声,豆浆机旋转的嗡嗡声。
窗外,深圳的鸟儿们也起床了,孩子们还在熟睡中。这琐碎平常,太过奢华,令人忍不住迷恋着它。
2024年3月31日(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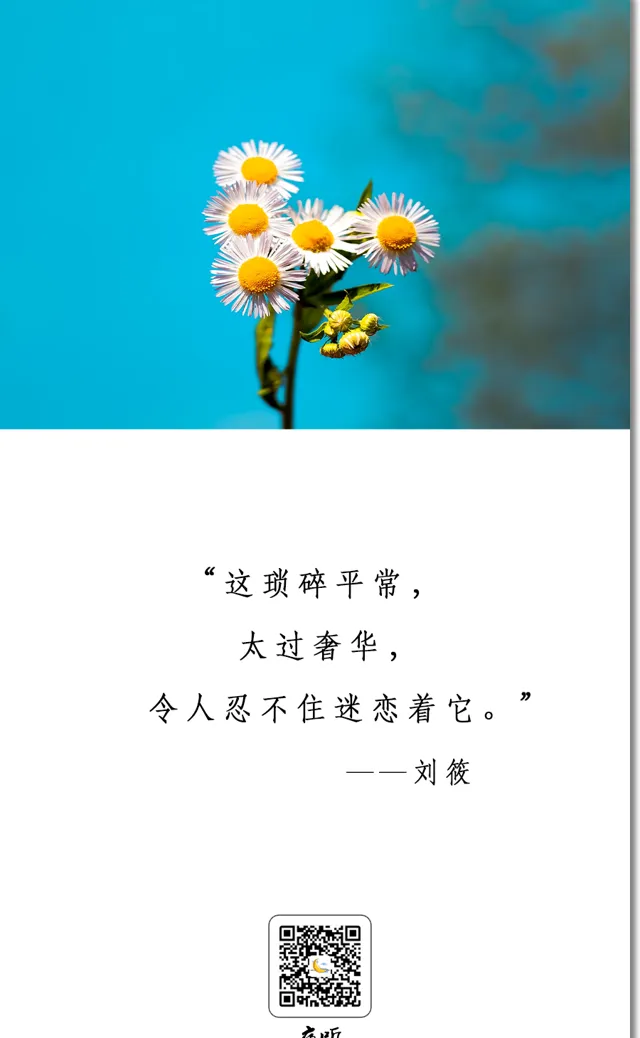
- E N D -
点击下方卡片 关注夜听
收听更多往期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