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區又稱「康藏」,是藏族傳統三大歷史地理區域之一。該區域地處橫斷山區,是青藏高原與川西平原、雲貴高原的重要連線地帶,既是藏族同西南各民族密切接觸交往的地區,也是歷代中央王朝經營和治理西藏地方的通道和關鍵區域之一。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石碩主編的【康藏史(古代卷、近代卷)】近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本書以通史體例,將康藏歷史置於歷代中央王朝、西藏地方及漢藏民族交流互動之中,系統梳理和呈現了該區域的歷史發展脈絡,是首部全面、系統勾勒和呈現康區整體歷史面貌的通史著作。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石碩教授進行了專訪,在他看來,「康藏史」意味著「連線」,是對認識中國古代歷史行程是一個豐富和拓展。
采訪|鐘源

▲ 石碩教授
澎湃新聞: 何為「康藏史」?康藏史的研究範圍是什麽?
石碩: 這個問題是認識和理解「康藏史」的基礎。「康藏」是一個習慣性稱呼,藏族傳統上將其分布地區分為「衛藏」、「安多」和「康」三大區域,這既是藏語三大方言區,也是三個不同的人文地理板塊。總體來說,「康藏」一詞的產生,大體有兩個含義:其一,「康」(khams)在藏語中是「邊地」含義,這是一個相對於「衛藏」(含義是中心)中心區域的概念。其二,清末已籌劃在原「川邊特別行政區」基礎上建立「西康省」,省會就選定在今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縣,但這個計劃因辛亥革命爆發而中斷。直到抗戰時期的1939年,鑒於該區域的重要性,才正式建立「西康省」。西康省第一任省主席是國民政府24軍軍長劉文輝。西康省的管轄範圍分三個大部份:一個「寧屬」,指原來清代四川省寧遠府的轄區,共8個縣,主要包括現在的涼山彜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一個是「康屬」,主要包括現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是藏族分布地區;一個是「雅屬」,主要指今天除名山之外的雅安市地區。所以,「康藏」這個傳統稱呼,也和西康省有密切關系。
康藏史的研究範圍與上述兩者密切相關,一是指藏語康方言的分布地區,大致為今四川甘孜、雲南迪慶、青海玉樹三個藏族自治洲和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俗稱「三州一地」;另一個則是指原西康省「康屬」範圍。當然,歷史上的康藏區域並不像今天的行政區域那麽準確、清晰,經常是比較模糊和籠統的,這一點特別需要指出。總之,「康藏」是沿襲歷史上的一個概念,用這個概念作書名,是出於尊重歷史的考慮。
澎湃新聞: 康藏地區有何特殊性?
石碩: 這個問題我們在研究和撰寫【康藏史】過程中,才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大體說來,康藏地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康區是一個地理過渡地帶,也是一個文化過渡帶。
康區地處橫斷山脈地區,這裏山川縱貫、東西駢列,是典型的高山峽谷地區。該區域處於中國第一級階梯向第二級階梯交接處,是青藏高原向雲貴高原及川西平原的地理過渡帶,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出水口,構成長江上遊的三條大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都從這裏流過,是水資源極為豐富的地區。康區地勢總體上西北高、東南低,但由於崇山峻嶺,這裏的氣候、植被垂直分布特點十分顯著,地理環境有顯著的阻隔性、分散性和多樣性特點。
康區正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基礎上形成的人文地理區域。自然與人文從來就息息相關,大致說來,康區的社會與人文方面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1、它是農牧過渡帶。從北向南,康區是從農牧混合逐漸向南部山地農耕的過渡,從西向東,則是農牧混合向農業地帶過渡。2、同地理環境的阻隔、分散和多樣相對應,康區也是中國文化多樣性、獨特性最突出的區域之一。比如,雖然同屬藏族文化,但金沙江流域、雅礱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等不同區域,均呈現了濃厚的地方特色。3、康區是民族走廊地帶,民族的流動、遷徙十分顯著。這又給該地區文化帶來了突出的復合性、相容性。4、康區在東西方向,是藏、漢民族交流互動以及西藏與中央王朝之間的連線通道和橋梁地區;在南北方向上,則是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之間發生聯系和相互溝通的孔道。
澎湃新聞: 從康藏史的視角考察中國古代歷史行程,有哪些獨特的發現?
石碩: 這個問題問得好。任何一個點、一個局部區域的研究,都應該問這個問題,即它對整體和全貌帶來哪些新認識?前不久,在京召開【康藏史】新書釋出及學術座談會,清華大學沈衛榮教授也提出這個問題,如何界定「康藏」?怎麽認識「康藏」的意義?不是從知識層面說明「康藏」一詞的含義,而是從中國古代歷史行程看,「康藏」意味著什麽?從「康藏」視角,我們能看到中國古代歷史行程中哪些過去看不到或被忽視的新東西?當然,從中原看邊疆,與從邊疆看中原,看到的東西肯定不一樣。
就【康藏史】撰寫的體會來說,首先,從康藏史視角,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歷史行程更具體、更為生動,對認識中國古代歷史行程是一個豐富和拓展。其次,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康藏史」對我們意味著什麽?我的答案是兩個字——「連線」。今天,翻開中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青藏高原幾乎占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青藏高原是怎樣一步步進入中國版圖的?這個問題的源頭,始於吐蕃王朝的東向擴張,始於吐蕃與唐朝之間近兩百年的密切交往與戰和關系。前面說過,康藏地區是青藏高原同內地之間的地理過渡地帶,也是文化過渡帶。過渡帶是什麽?是「結合部」,也是「連線帶」。康藏地區,正是這樣一個「連線帶」。如果我們不了解「康藏史」,缺失了這個「連線帶」,我們就很難理解西藏乃至青藏高原地區為何一步步進入中國政治與文化體系。康藏地區,既是地理連線帶,也是民族連線帶,還是文化連線帶。所以,我認為,【康藏史】的主題,就是兩個字——「連線」。它是我們理解青藏高原怎樣一步步進入中國古代歷史行程的關鍵區域。

▲ 田野考察中的石碩教授
澎湃新聞: 7世紀前康區的歷史源流和社會狀況是怎樣的?
石碩: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至少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康區已有古人類活動蹤跡。進入新石器時代,康區的人類活動遺跡已相當豐富。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康區的分布較為廣泛。目前,在康區西部的瀾滄江流域地區、東部大渡河上遊地區均發現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二,新石器時代,康區已出現了一些文化堆積極厚的大型聚落遺址。這些大型聚落遺址延續的時間相當長,有的甚至達千年以上。這表明,新石器時代在康區這一橫斷山脈高山峽谷地區,文明發展水平並不遜於周邊其他地區。當我們把康區新石器時代文化放在更大的地域空間來審視其與周邊新石器文化的聯系時,可以發現一個顯著事實——康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同黃河上遊甘青地區新石器文化存在廣泛而緊密的聯系。換言之,在康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存在著大量來自黃河上遊甘青地區的文化因素。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彩陶和人工栽培作物粟。根據對東亞人群Y染色體單倍型的型別及頻率分布規律的調查,甘青地區的原始居民中的一支大約在6000年前很可能由於氣候急變,即驟然轉向寒冷幹燥而開始由南下向橫斷山脈地帶遷徙,並由此產生了漢語語族和藏緬語族人群的分化。這些經由不同的路線和通道南下的新石器時代居民不僅是康區新石器時代文明的主要拓荒者和創造者,也是藏緬語族最早的祖先人群。
繼新石器時代文化之後,康區古代先民留下的普遍分布的考古遺存,是一種被學術界稱作「石棺葬」的墓葬文化。石棺葬在橫斷山區分布地域甚廣,不僅在瀾滄江上遊流域、金沙江上遊流域、大渡河中上遊流域和滇西北地方均有分布,在岷江上遊地區、青衣江流域乃至滇中地區也均有廣泛的分布。目前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主要把分布於大渡河以西(漢代的「旄牛僥外」地區)的川西高原地帶,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雅礱江和金沙江諸流域的石棺葬,同漢代活動於該區域的白狼、槃木、樓薄等部落相對應。在漢代白狼、槃木、樓薄等部落活動的所謂「旄牛僥外」區域,即今天雅安以西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確發現了數量豐富的石棺墓葬。史籍對白狼部落的記載相對豐富,白狼部落也是漢代康區範圍最有名、最重要的部落。白狼部落應是以巴塘一帶金沙江流域地區為中心,分布地域遼闊且大體覆蓋了今川西高原範圍的一個大部落,人口規模也較為可觀。從其在後世所具有的廣泛影響來看,白狼部落無疑是漢代(乃至唐以前)康區最大和最重要的部落。
白狼部落最為有名的是留下了用白狼語記音的三首「白狼歌」,這是目前留存下來的最早的古藏緬語語料。如果說,新石器時代是黃河上遊人群向南和向西遷徙的第一個的高潮,那麽,在進入歷史時期以後,尤其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代,黃河上遊地區人群向西和向南遷徙的趨勢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續,並形成藏緬語民族南遷的第二個高潮。這可以解釋漢代分布於康區橫斷山脈地帶的白狼部落所操的白狼語,何以會同藏語之間存在親緣關系。漢代康區的白狼部落所使用的語言同藏語之間存在親緣關系的這一事實,也成為後來康區與西藏地區在文化面貌和語言系屬上發生密切聯系的基礎。
在公元七世紀以前,西藏地區已與包括康區在內的川西高原地區存在密切聯系與交往,一個突出現象是源自於象雄的苯教文化由西藏向川西高原地區的傳播。從東漢時期川西高原範圍出現被稱作「邛籠」的碉這一建築來看,瓊氏部落由西藏瓊布遷入川西北和康區的時間至少可上溯到西漢中葉至東漢時期,比公元7世紀初吐蕃王朝興起早了約400年。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西藏腹心地區部落與康區部落之間的聯系,還體現於兩地之間可能存在部落間的聯姻。無論是敦煌古藏文寫卷P.T.126 Ⅱ所記遠古時代的「穆」、「恰」聯姻,還是「獼猴」與「羅剎女」結合衍生藏人的傳說,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均反映了在藏人的記憶中,在「遠古之初,辟荒之始」,曾經發生過藏地腹心地區氏族與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區即康區地域的氏族部落之間的聯姻。
隋代,在康區地域出現了一個較大的政權,這就是【隋書】和【北史】所記載的「附國」。附國同漢代白狼部落之間顯然應存在繼承性。在附國的東北方向分布的眾多部落中,還出現了名為「千碉」的部落。這說明,在隋代,來自西藏地區的苯教文化在康區和川西高原地域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也進一步說明,在公元七世紀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康區在文化以及信仰上已與西藏地區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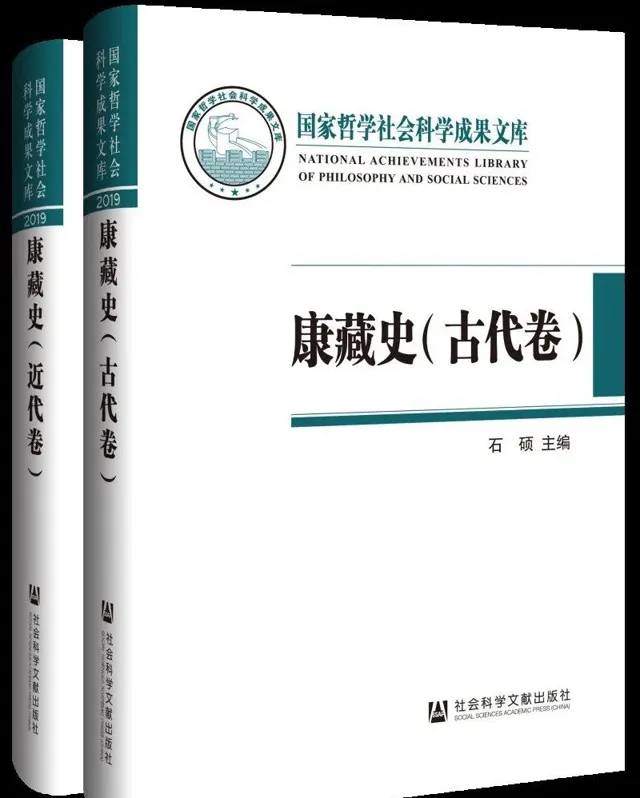
▲ 【康藏史(古代卷、近代卷)】
澎湃新聞: 吐蕃崛起後,康區和吐蕃有著怎樣的互動?
石碩: 公元七世紀初,當松贊幹布統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之際,介於新興吐蕃與唐朝之間的康區地域,乃是一個遼闊而又薄弱的中間地帶。唐與吐蕃之間的附國、吐谷渾、黨項、白蘭及松外蠻等都處於相對自主的狀態。貞觀十二年(638年),吐蕃發動了直接針對唐朝的松州戰役。吐蕃發動松州戰役旨在謀求與唐聯姻,並無與之進行大規模軍事對抗的意圖。松州戰役是唐蕃間的第一次正面交鋒,不但向唐展示了新興吐蕃王朝的實力,由此也揭開了唐蕃之間在劍南、西川一帶長達兩百多年的爭奪戰的序幕。
在7-9世紀,吐蕃與唐朝在西南的戰事主要集中於劍南西川一帶,尤其是集中在松、茂、黎、雅、巂等各州一線,雙方在此進行了長期的拉鋸戰。吐蕃對劍南西川地區的進攻主要分南、北兩條線。北線穿越橫亙於康區北部的白蘭地界,經草原地帶長驅直入,直達今川西北大渡河上遊及岷江上遊地區。從公元八世紀起,在吐蕃征服南詔並與之結盟以後,南下滇西北、再由川西南一帶北上黎、雅地區,也逐漸成為吐蕃進攻劍南西川的南線。南線主要是以南詔為依托,多為吐蕃與南詔軍隊聯合作戰。南線在安史之亂後逐漸活躍,成為吐蕃在巂州、黎州、雅州一帶與唐交鋒和爭奪的主要進攻路線。在安史之亂後,吐蕃由南、北兩條路線向劍南西川地區的進攻,最終形成了南、北呼應和貫通之勢。
吐蕃實施了對康區部落的長期役屬與控制。比如蘇毗傳統地域最初主要在以今昌都、玉樹為中心的康區西部地區,但隨著吐蕃王朝的向東擴張,蘇毗人在東部地區廣為擴散,不但大量分布於河西隴右地區,在吐蕃末年,一部份駐守河隴地區的蘇毗人亦曾由西北南下,向康區一帶擴散。吐蕃征服的藏東北一帶的黨項、白蘭、多彌等,甚至可能包括蘇毗部落,這些部落所操的語言和吐蕃本部所操的藏語可能是不一樣的。這表明吐蕃向青藏高原東部方向的擴張,實際是把許多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甚至不同信仰的部落收入麾下,並把它們在政治上、軍事聯系為一體。吐蕃對康區東部東女國的征服與控制呈現兩個特點:一是階段性,其部落被吐蕃「役屬」主要是在「中原多故」即安史之亂以後;二是有限度,這些部落政權因介於吐蕃與唐朝之間,當其不堪吐蕃的「役屬」時,往往投唐內附。即便投唐內附以後,它們也時常「潛通吐蕃」,故被形象地稱作「兩面羌」。吐蕃向東部擴張過程中,所征服並與之結盟的最大政權與部落,自然要算其東南方向的南詔。南詔與吐蕃的聯盟關系,事實上正是吐蕃向東擴張征服東部地區眾多政權與部落並與之結成的聯盟關系的一種主要形式。
目前在康區所發現的吐蕃時期的遺跡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在金沙江流域地區即今藏、川、青交接地帶發現了數量眾多的吐蕃時期遺留下來的佛教摩崖造像、石刻等與佛教類的遺址和遺跡。從目前在藏東及康區境內所發現的佛教摩崖造像及石刻題記看,佛教真正比較大規模地由吐蕃傳播到康區,主要是在九世紀初期即赤德松贊時期。今從藏、川、青交界的金沙江流域發現十余處吐蕃時期佛教摩崖造像及石刻題記看,康區西部即今西藏昌都、青海玉樹、四川石渠一帶的金沙江流域應是佛教自吐蕃向東放射線和傳播的一個重要通道和門戶地區,是吐蕃佛教向東傳播的重要基地。傳說及後弘期藏文文獻反映毗盧遮那在東部地區傳教產生廣泛影響,從金沙江流域地區發現十余處吐蕃時期佛教摩崖造像均以大日如來佛為中心看,吐蕃時期康區特別是金沙江流域地區的佛教當主要以密教為特點。透過對吐蕃在康區的活動遺跡進行梳理,我們大體可以得出以下幾個認識:一是八世紀末九世紀初,佛教在吐蕃已十分興盛,僧人已進入吐蕃的權力中樞;二是吐蕃的東擴,佛教也進入康區南北各地;三是吐蕃曾利用宗教、軍事等手段有計劃地對康區進行經營;四是吐蕃文化吸收了康區當地、漢地以及尼泊爾和印度等南亞地區的文化成分。
澎湃新聞: 康區是如何被整合進入藏地三大傳統區域的?
石碩: 藏地「三區」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從現有資料看,主要與元朝對藏地的統治與管理直接相關。元朝先後設定了三個軍政機構來實施對藏地的統治與管理,它們是:烏思藏納裏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土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和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這三個行政區不但奠定了藏人「三區」概念的基本輪廓,對逐漸形成「三區」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過一篇論文【藏族三大傳統地理區域形成過程探計】(【中國藏學】2014年第3期),談得比較詳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一步參閱。
在吐蕃王朝崩潰以後,原駐守吐蕃王朝東部地區的吐蕃軍隊及隨軍部落,因無法返回故裏,大量吐蕃人和吐蕃奴部在原屬吐蕃東部疆域的康區一帶廣為擴散,形成了大量吐蕃人與原為吐蕃屬部的康區各部落居民相互雜處、就地耕牧繁衍的局面。在吐蕃所征服的東部地區,從各種不同稱謂的部落以及被稱作「夷」「羌」及「羌之別種」的人群,進而演變為「吐蕃遺種」或「吐蕃贊普遺種」。其原因和基礎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吐蕃時期,吐蕃王朝對東部地區特別是康區的各部落和人群進行了長達百余年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使它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熏染。
二、在吐蕃王朝解體以後,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於康區一帶,遂與當地原為吐蕃屬部的諸羌居民相雜處,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發展的道路。
三、公元10世紀以後,隨著後弘期藏傳佛教的興起,藏傳佛教不僅在衛藏地區得到復興和發展,同時也不斷由衛藏地區向東部的康區一帶傳播和滲透,最終使得康區居民與衛藏地區居民之間在語言文字、心理素質及文化面貌上逐漸趨向一致。
在後弘期初期藏文文獻中開始出現了「康」這一概念。把指稱「邊地」的「康」(khams)作為與「衛藏」中心區域相對應一個地理區域來看待,這實際上反映了在吐蕃王朝解體以後,在藏地的觀念中,也在進行一個整合。這就不僅仍然將衛藏作為一個中心區域來看待,同時也把過去吐蕃王朝占領和控制的整個東部地區稱之為「康」,即籠統視為「邊地」。也就意味著,在這一時期,盡管吐蕃王朝已不復存在,但在藏地尤其是衛藏人的觀念中,仍繼承了吐蕃王朝的政治與文化遺產,在地理上和文化板塊上仍將整個遼闊的東部地區視為與「衛藏」中心區域相對應的「邊地」。這說明一個問題,在公元10世紀佛教後弘期以後,在藏人尤其是佛教高僧的觀念中,也已逐漸將整個遼闊的東部地區作為與「衛藏」中心相對應的「邊地」納入其體系之中。
在吐蕃王朝崩潰以後到宋元時期,青藏高原地域除悄然而緩慢地發生的人群與文化的整合外,同時也發生了另一個重要變化,即青藏高原的地域整合。確切的說,是衛藏、安多和康三大人文地理區域格局的逐步形成。很大程度上,這兩種整合之間存在密切的內在關聯,二者是互為表裏且相輔相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人群與文化整合逐步達到一個新階段,才為地域的整合即新的地緣格局的出現奠定了基礎。而新的地緣格局的形成和出現,正是不同人群與文化相互整合的一個結果。
澎湃新聞: 藏文史籍中稱衛藏為「法區」,安多為「馬區」,康為「人區」。「人區」的內涵是什麽?
石碩: 對藏族三大傳統區域各自的特點和差異,藏文史籍中有一個簡約而精辟的概括,稱衛藏為「法區」,安多為「馬區」,康為「人區」。這就是說,衛藏的特色是「法」即宗教;安多的特色是「馬」即牧業;康的特色是「人」。藏族的民間諺語中還有這樣的表述:「衛藏人是熱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鬥士,安多人會做生意。」這些均反映了藏人自身對於三大區域之特點的歸納和認識。
民間諺語所稱「康巴人是好鬥士」,或可幫助我們對於「人區」的理解。在藏族地區,常常普遍以「康巴漢子」一詞來指稱康區的男人。「康巴漢子」在衛藏和安多地區藏人心目中,也往往以體形高大、性格強悍、好鬥、講義氣著稱。
以下三個事實或有助於我們對康被稱作「人區」的理解:
1、根據體質人類學測量結果,藏人被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體質型別:藏A型和藏B型。藏A型又稱「僧侶型」。其特點是短頭型、面孔寬、身材較矮小;藏B型又稱「武士型」或「康區型」。其特點是長頭型,面孔相對窄,身材較為高大。
2、10世紀以後,在康區地域卻產生了一部【格薩爾】英雄史詩。【格薩爾】史詩所彰顯的是對人性的頌揚。它以歌頌英雄氣概、勇敢、積極進取、不畏強暴、敢愛敢恨等這樣一些體現人性的因素和內容為基調。
3、康巴人具有個性張揚、強悍好鬥和敢於開拓進取的性格特點。藏族民間諺語「康巴人是好鬥士」,頗能反映康巴人的性格特點。從歷史上看,康區人的強悍好鬥特點表現得十分突出。近代以來,康區始終是各種武裝沖突和暴力事件頻發地區,如「大小金川事件」「瞻對事件」「巴塘之亂」「布魯曼起義」等等。康巴人的這些性格特點與【格薩爾】英雄史詩所彰顯的精神氣概頗相契合。
在後弘期佛教高僧德的語境和地理觀念中,把原吐蕃王朝的疆域劃分為「衛、藏、康」三個部份,乃是當時一種較為普遍的習慣。其中最早記載藏地「三區」概念的是大司徒·絳曲堅贊的【朗氏家族史】。不過,藏文史籍中時間最早、最清楚地記載藏地「三區」的,要數達倉宗巴·班覺桑布寫成於1434年的【漢藏史集】,對「三區」範圍的描述及分別將之稱作法區、人區和馬區。各藏文史籍的記載基本一致,大抵均承襲【漢藏史集】。

▲ 田野考察中的石碩教授
澎湃新聞: 在不斷的和周邊區域的各種勢力以及中央政權有著頻繁密切的交往、互動,康區的文化、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有怎樣的改變?康區的文化、信仰、習俗等對西南其他各民族有怎樣的影響?
石碩: 歷史上起源於西北地方的古藏緬語民族系統(習慣上被稱作「氐羌民族系統」)主要是經康區南下而逐漸散布於整個橫斷山脈地區。同時歷史上的百越、壯傣和苗瑤等南方民族系統的人群也有經此民族走廊北上遷徙。康區自古以來無論在南北方向還是東西方向上都是多民族的流動與交融薈萃之所。眾多民族及族群在這裏頻繁地發生接觸、沖突、融合與互動。民族走廊這一特殊背景構成了康巴地區民族分布眾多、民族構成復雜多元的局面。目前,康巴地區的主體民族雖為藏族,但同時也有漢、彜、蒙古、納西、羌、回等多種民族,他們均形成了與康巴藏族相互比鄰或混居的局面。而單就康巴藏族的形成來看,其成分也是相當的多元與復雜。
康區的藏族是以漢代以來當地原有的氐、羌、夷等眾多民族成分為主體,自吐蕃向康區擴張以來不斷受到吐蕃和藏文化的融合與同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康區藏族的形成大致經歷了如下幾個演變過程:吐蕃時期,吐蕃王朝對康區諸羌各部進行了長達二百余年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使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吐蕃王朝以後,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於康區一帶,遂與當地原為吐蕃屬部的諸羌居民相雜處,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發展的道路;公元10世紀以後,隨著藏傳佛教後弘期興起,藏傳佛教不斷由衛藏地區向康區傳播和滲透,從而使康區居民與衛藏地區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質和語言文字上逐漸趨於一致。自12世紀以來,由於民族間的遷徙、沖突與交融,也陸續有若幹民族成分以各種方式融合到康區藏族之中。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漢、彜、回、蒙古、納西、羌等等。正因為康巴藏族在族源構成上的復雜、多元特點,所以今天在康巴地區藏族內部仍存在著眾多支系。這些人群支系不少仍使用著自己的母語,如在康巴地區有講木雅語的木雅藏人;有講道孚(爾龔)語的藏族自稱「布巴」;有講紮巴語的藏族自稱「紮巴」;有講貴瓊語的藏族自稱「貴瓊」;有講卻域語的藏族自稱「卻域」等等。這些不同支系的藏族彼此在文化和風俗上均存在相當差異。這種在同一民族內部存在眾多人群及語言支系的情況極具典型意義,是康區作為民族走廊地區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
康區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藏、漢民族的互動與交融。清代、民國時期大量遷入康區的漢人迅速同當地藏人發生密切交融,交融的主要途徑是通婚。由於清代民國時期進入的漢人主要為官兵、商人、墾民和各類工匠,均為單身男性,加之邊地遙遠,環境艱苦,故漢藏通婚往往成為遷入漢人的普遍選擇。清代民國時期大量漢人遷入康區所帶來的漢、藏互動,其結果主要表現為「漢」向「藏」的融入。一方面,因為漢藏通婚和適應環境的需要,落籍當地的漢人幾代之後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這些漢人又把漢文化因素帶入當地的藏文化之中,形成當地人所說的「倒藏不漢」「漢人不純,藏人不藏」即漢、藏雜糅的文化狀態。
康區從元代起在原部落的基礎上開始形成眾多土司。明清時期康區範圍的大小土司已多達百余個,其中最大的有德格、明正、巴塘、理塘四大土司。這些土司受中央王朝冊封,其權力在家族內部世代相襲。土司之間彼此互不統屬,並常為爭奪地界、屬民發生沖突。在清末民初改土歸流過程中許多土司雖被廢除,但因政局動蕩,土司統治在很多地區紛紛得到恢復。康區以土司為主的多元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所以,歷史上康區是一個政治多元地區,從未形成統一全境地方的政權。這種政治多元與地域分割性密切相關,今天康區不少地界和草場糾紛,也同土司時代的傳統地界密切相關。
澎湃新聞: 康藏地區的基礎社會形態如何?普通百姓的社會生活是怎樣的圖景?
石碩: 作為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山峽谷地區,康區就如同是一個密集的地球皺褶地帶。在這個皺褶帶中至今積沈和保留著許多古老而獨特的社會形態、文化現象與文化遺存。今天在川、滇交界的瀘沽湖沿岸的摩梭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兩縣交接處鮮水河流域的紮巴人中,仍完整地延續著以母系為中心的家庭結構和「走婚」形態。與母系中心社會相對應,康區也保留不少父系氏族的社會組織形態。在金沙江河谷深處的三巖地方保存著一種被稱作「戈巴」和「帕措」的父系社會組織。在今康北牧區還完整地保留著一種以「骨系」(父系血緣)為紐帶的遊牧單位和血緣組織。同時在康巴地區至今還存留著相當數量獨立和尚待認識的語言,這些語言在當地被稱作「地腳話」,其使用人群多則上萬人,少則僅有幾百幾千人,他們與外界交流時多使用藏語、彜語或漢語,回家則說「地腳話」。這些有著「活化石」之稱的「地腳話」引起語言學者的廣泛關註與興趣。在康區迄今還保留著大量獨特的古代碉樓,即【後漢書】中已見於記載的「邛籠」。在今大渡河上遊的丹巴縣境內古碉數量之密集著實令人驚嘆,號為「千碉之國」。這些石碉今天雖已喪失實際功用,但作為一種獨特的歷史遺產其文化價值與豐富的社會內涵正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康區保留下來的宗教種類及各種原始宗教形態也極為豐富和復雜多樣。康區不僅集中了現今藏傳佛教的所有教派,甚至連歷史上已完全消失的一些教派,如覺囊派等以及佛教傳入以前存在於藏地的最古老苯教也均在康區有較好的保留。金川一帶還流行「入寺信黃教,在家信苯教」之俗。即便是在藏傳佛教覆蓋地區,在民間的社會生活層面也仍大量保留著可稱作「底層」的各種原始宗教成分。在康區不少地方至今仍普遍存在著一些不屬於任何寺廟被人們稱作「工巴」「達巴」的民間巫師。一些地區還保留有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書等等。所以,古老原始文化的大量存留可以說是康區一個突出特點。
在藏族三大傳統區劃中(三大方言區)中,康區無論是在語言、服飾、建築、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婚姻形態、社會型別等各個方面呈現的多樣性、豐富性堪稱首屈一指,其中任何一個方面均可用「異彩紛呈」來形容。康區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在流傳於當地的諺語中也得到充分反映:「一條溝,一種話」;「每條溝有自己的習俗,每條溝有自己的土話」;「五裏不同音,十裏不同俗」;「一山一文,一溝一寺,一壩一節」。這些諺語是對康區文化多樣性的生動概括。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即是一個典型的多元文化薈萃之所,在不足幾平方公裏的康定城內,就集中了天主堂、清真寺和藏佛佛教主要教派的各大寺院。在昌都芒康縣鹽井區則形成基督教、藏傳佛教與東巴教相互並列的和諧局面。
澎湃新聞: 清朝政府對於康區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強了,清朝采取了哪些有別於前朝的管理方式?
石碩: 清朝勢力進入康區是針對吳三桂與康區之蒙古和西藏結成同盟為起點的。明末,來自北方的和碩特蒙古逐步控制了整個青藏高原,康區大部份地區統治權都掌握在和碩特部手中。對於吳三桂,蒙藏雙方雖未給予支持,但中立態度使得吳三桂在與清朝的對抗中在康區獲得相對寬松的環境。由於清前期面臨北方準噶爾蒙古這一心腹大患,為了顧全和穩定大局而采取「捍準夷而扶持和碩特」的政策,因此對於和碩特在康區的擴張並未采取軍事措施,而是多以政治手段介入。三藩之亂肅清後,清朝在西南地區局勢漸穩,對康區的態度也逐漸發生改變。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發生了打箭爐蒙古營官喋巴昌側集烈將打箭爐地方內附土司蛇蠟喳巴打死的惡性事件。康熙帝令提督唐希順發兵進剿,史稱「西爐之役」。西爐之役後,清朝在康區力量大振幅向西推進,控制了雅礱江以東地區。
西爐之役後,清朝收復打箭爐地方,對歸附的土司授以官職,編入清朝管理體系。隨後,清朝也開始在打箭爐地區駐兵的行動,正式將化林營移駐打箭爐。自此,打箭爐開始成為從內地通往西藏大道上的重要據點。清朝經營打箭爐的重要舉措乃是在大渡河上修建了瀘定橋,這也為清朝開拓從內地經打箭爐通向西藏的道路提供了可能。瀘定橋的建成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則是作為漢藏茶葉貿易中心的打箭爐的興起。自吐蕃時代起,漢、藏之間形成以大渡河為分界的傳統,到明末清初,因西爐之役、瀘定橋建成和清朝控制打箭爐以及漢藏茶葉交易市場的西移等事件,漢、藏之間以大渡河為傳統分界的格局被打破。漢藏分界向西推移,跨越大渡河,移至打箭爐地區。
促使清朝進一步向康區擴充套件勢力,特別是向打箭爐以西開拓的一個重要因素,則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發生的新疆準噶爾部策妄阿喇布坦侵入西藏事件。清朝最終選擇從成都-打箭爐和西寧分南、北兩個方向進兵西藏,並積極展開對由打箭爐入藏道路的探查、籌劃。「驅準保藏」軍事行動所導致的對打箭爐入藏道路的開拓,很大程度上成為清朝治理西藏取得重要進展的一個轉折和標誌,這突出體現於以下兩點。
其一,打箭爐入藏道路的開拓,使清朝進藏道路由過去以西寧一路為主開始轉向以南路為主,同時也成為清朝治理西藏及藏地戰略依托及重心逐漸向康區轉移的一個標誌。
其二,在開辟由打箭爐入藏道路過程中,清朝以此為契機逐漸控制了康區,並使康區日漸成為清朝治藏的前沿與依托。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蒙古和碩特部羅蔔藏丹津起兵叛亂後,清朝在平定羅蔔藏丹津叛亂中,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即是防範叛亂向康區的蔓延。其采取的具體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對康區各緊要之地派兵駐守;二是對康區各地的番眾進行廣泛招撫。從某種程度說,羅蔔藏丹津叛亂實際上為清朝進一步控制康區提供了良好契機。由於在平定「羅蔔藏丹津叛亂」中,清朝對康區各緊要之均地派兵駐守並對康區各地番眾廣泛進行招撫,故在「羅蔔藏丹津叛亂」平定後,康區整體政治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和碩特蒙古在康區的勢力基本被驅逐,其對康區的影響力也大為下降。「羅蔔藏丹津叛亂」平定之初,年羹堯上奏【禁約青海十二事】以及【平定羅蔔藏丹津善後事宜十三條】,對平叛的善後措施提出了系統方案,清朝基本采納了其建議。其中有關徹底肅清和碩特蒙古在康區的影響,以防止其卷土重來和全面加強清朝對康區控制的舉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清朝以盟旗制改造和碩特蒙古,杜絕了蒙古勢力再次控制康區的可能。
第二,設定官職,冊封土司,加強對康區番族的管理。1727年,西藏貴族噶倫之間因權力爭奪而發生沖突,主持藏政的首席噶倫康濟鼐被殺,「衛藏戰爭」爆發。清朝再次經由康區派軍入藏,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清朝在此次進藏過程中對康北地區土司又重新進行招撫;二、此次清軍南路入藏,四川路由打箭爐-霍爾-甘孜-德格一路與松潘-郭羅克-霍爾-春科河一路會和後在察木多與雲南中甸-阿墩子-察木多路之兵丁會和,而打箭爐-理塘-巴塘-察木多一路負責備辦糧草事宜,這是康區在劃歸內地管轄後第一次四路協調進兵。這實際上意味著由康區進藏的道路已經連線成為一個體系,康區聯結內地與西藏的功能已經相對完備,在清朝治藏戰略中的地位更加得以凸顯。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第二次大規模在康區冊封土司,這使得清朝在康區土司制度得以重新確立。經過這一次的土司設定,加上康熙年間「西爐之役」後設立的土司56員,康區共有大小土司一百二十余員。清朝此次在康區大規模設立土司,是在整個西南土司改土歸流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在康區選擇設定土司實際上是充分考慮了康區的現狀,又與川滇藏劃界密切結合起來一同推進。這些土司的設定是清朝加強康區控制的需要,客觀上也使得清朝對康區的統治進一步加強。
平定「羅蔔藏丹津叛亂」後,清朝還在藏地采取了一項意義重大和影響極為深遠的措施,這就是對藏地行政區劃的劃分。經過年羹堯的籌劃以及嶽鐘琪、周瑛的實踐,清朝完成了康藏劃界。在清朝治理西藏乃至整個藏地的歷史上,這一舉動有著標誌性意義,它意味著清朝對西藏的治理進入到以行政建制進行規範的階段,同時也意味著康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在清朝治藏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首先,康藏劃界以清除蒙古在康區的影響。其次,保障川藏道路暢通。
第三,以「番民」內屬為目的。劃界自雍正三年開始,到雍正十年結束。最終,確定了康區與西藏之間的界線,也在行政區劃上確定了康立的地位。康藏劃界將康區大部份直接劃歸四川省,徹底阻斷青海蒙古和西藏地方對康區的覬覦。劃界也使得清朝開始全面控制康區,康區真正成為清朝治藏的前沿與重要依托。
澎湃新聞: 康區的大小土司對於改土歸流有著怎樣的因應?
石碩: 康區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發生在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期間。歷經清朝百余年間的羈縻經營,在政治上呈現出多元復雜的狀況。至清末,川邊地方歸屬土司管轄者僅余十分之五,由呼圖克圖掌控者十分之一,部落形態的牧區為十分之三,西藏控制區域占十分之一。川邊的改土歸流動行程正式啟動始於川滇邊務大臣創設後,以自願和強制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康區大小土司對改土歸流的態度不一,既有抵制,比如川邊各地土司獲知趙爾豐返川後,暗中聯絡,抵制改流。六月,魚科土司抗不繳印,聯同下羅科百姓滋事。明正土司甲宜齋得到鄉城桑披寺普仲乍娃之侄曲批暗助策劃,先後聯絡鄉城、道塢渣壩三村土百戶、甘孜孔撒土女央機,調集木裏、九龍、巴底、巴旺各土司,意圖聚兵恢復土司舊制。孔撒土女央機密呈其謀,趙爾豐急令統領鳳山率兵赴鄉、稻,鎮撫木裏、九龍,電令中路統領劉亥年赴爐,以扼其勢。傅嵩炑分兵往攻魚科,土司降登宜錯逃往上羅科被殺。也有主動改流,比如德格土司爭襲案中,土司多吉僧格多次主動請求呈繳印訊號紙,納地改流。因此,清朝覆亡後,剛剛建立起的川邊政治新秩序,因喪失軍事力量的支撐和政治局勢的動蕩,迅速土崩瓦解。川邊各地土司紛紛起事復辟,陷於混亂狀態。

▲ 田野考察中的石碩教授
澎湃新聞: 近代以後,康區的社會文化生活有著哪些顯著的改變?
石碩: 康區在近代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藏密在內地的廣泛傳播,推動了內地佛教的改革和復興,溝通漢藏文化,融洽漢藏民族感情。漢僧遊藏學法和藏僧內地傳法是促成藏密在內地宗教界深入人心的雙重動力和實作途徑。康區在漢僧遊藏學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連線和中介作用。以多傑覺拔格西和諾那呼圖克圖為代表的康區高僧的內地傳法活動,則表明康區在整個藏密傳播內地過程中已不限於單純的媒介和通道功能,而是主要的推動力量來源之一。在毗鄰康區的川渝地方,漢藏教理院、西陲文化院、近慈寺「護國金剛道場」、重慶佛學社、四川佛學社等一系列重要佛學社團組織和學校的組建,正是緣於康區與川渝之間的宗教地緣優勢。這些均說明,在近代漢藏民族關系交往史、文化交流史上,康區扮演著重要角色。
近代康區的商業貿易在維系內地、西藏及東部藏族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因康區社會大多屬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發展滯後,物物交換占主導。近代康區貿易的變化突破了川藏商貿傳統的壟斷地位。在印茶、英貨的侵銷的挑戰情勢下,因新辟交通路線開通等因素的推動,滇藏貿易及甘青回商主導的青康貿易的日益崛起,改變和重設了康區整體的商業格局。
近代漢人移民入康改變了當地民族構成與分布格局,漢藏民族交融與互動直接影響了近代康區社會和文化的總體面貌。「利美」(即不分教派)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康區開創出各教派互動、調和與對話的包容宗教環境,對邊緣、弱勢教法的保存傳承及本土文化的重新發掘,更是賦予其「文化復興」的內涵。近代康區的傳統文化藝術內容包羅永珍,包含歌謠、史詩、繪畫、戲曲等,既與其他藏族地區有相仿之處,也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已趨成熟的各種傳統文化藝術以歷史的積澱為基礎,在近代康區新形勢下獲得新的發展,不斷吸納和融合了許多新元素。近代康區經受了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社會的劇烈變革,城鄉、農牧之間的社會生活軌跡因受到時代變遷的沖擊,顯現出較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還表現在社會階層和不同地域之間。當城鎮內新舊社會生活元素不斷碰撞、雜糅和融合的同時,遠離城鎮和交通沿線的鄉間,尤其是廣大牧區還基本上延續著千百年來的傳統生活模式。
澎湃新聞: 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您是否有持續性的田野考察?這種回到歷史現場的方法,對於史學研究有著怎樣的作用?
石碩: 是的。田野是認識民族的基礎,無論民族史還是民族學的研究,均離不開田野考察。我以及我們團隊成員每年都要到康區進行田野考察。回歸歷史現場,細致考察多民族文化相容特點,以今日康區多民族文化多樣性、包容性等現狀,反觀康區民族歷史發展的總體脈絡。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認識一些長期在康定工作、生活的漢族朋友,他們早上大多有喝酥油茶的習慣。漢族女士們也大多有1-2套藏裝,每逢藏歷年或其他藏族節日盛典活動,他們都會穿上藏裝參與其中。當地藏傳佛教寺院的重大佛事活動以及轉山會等,他們也都像歡慶自己的節日一樣,積極喜慶地參與。我初到康定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最初見到這種情形曾暗自好奇,並小心翼翼地問過他們,讓我羞愧的是,他們對我的問題反倒有些詫異,說:「在我們這裏都是這樣。」後來,去康定的次數多了,時間久了,我發現康定的藏族人也都如此,他們也過春節、過中秋節、掛春聯,平時穿漢裝,按漢人的習慣做事。其實,在康定這種漢、藏民族長期共居的邊城,當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明確的民族界限,他們的頭腦中也很少有「漢族」「藏族」這樣的觀念和界線,與民族身份相比,他們更容易接受「康定人」這樣的身份和稱呼,他們的話語中,常常是「我們康定人」「你們成都人」等等。也就是說,在康定人心目中,地域觀念及認同明顯超越了民族觀念與界線。
這種局面的造成,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歷史的原因。凡土生土長的康定人,相當一部份藏族人和漢族人其祖上以及祖輩或父輩中,大都或多或少存在漢、藏聯姻通婚的情況。尤其是清代以來,由於大量茶葉商人及漢人移民進入康定,時間一久,他們逐漸在當地落籍,加之與當地藏人通婚,有相當一部份即變成了今天當地的藏族。這種復雜的歷史背景,造成了要嚴格分清誰是漢族,誰是藏族,是一件頗為困難和麻煩之事,也完全無此必要。二是現實的原因。在康定城內,漢族和藏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往來極為密切,從單位同事,到同學圈、朋友圈、親戚圈,漢、藏民族之間的交往、接觸,就像空氣一樣,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在這樣的環境裏,要隨時隨地分清誰是漢族,誰是藏族,不但麻煩累贅,在行事過程中也平添阻力和困擾。所以康定的朋友調侃我說,「老想分誰是什麽民族,只有你們這些外面來的、做民族研究的人才這樣想。」這話讓我感到有些羞愧,同時也讓我反思和感悟。「民族」真有那麽重要嗎?面對民族交往與民族關系,康定人所選擇的這種主觀上「不分民族」的態度,可能恰恰是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高超的智慧。
澎湃新聞: 康藏史今後還有哪些新方向可以努力?
石碩: 【康藏史】的完成,不是康藏研究的終點,而只是一個起點。【康藏史】在資料完整性、豐富性上有較大突破,是一部集資料與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康藏史基礎性著作。但是康藏史資料存在許多區域和時段上的缺環和空白,為今後繼續推進康藏史研究預留出空間:1、探索歷史上康區各民族之間交往、接觸的「相處之道」;2、繼續註重結合多語種文獻史料,對康藏地區歷史發展脈絡進行更為細致的探討,比如立足於藏文史料,論述囊謙、德格等區域的歷史文化發展歷程。
(采訪內容得到鄒立波副教授的協助。)

本文先發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歡迎點選下載「澎湃新聞」app訂閱。點選左下方「閱讀原文」即可存取全文。
投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