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中國婦女第一次群眾性地紀念三八節活動是1924年,距今剛好100年。為了紀念今年的婦女節,我們回訪了采訪過的10位女性,其中有猛獸飼養員、卡車司機,有科學家、作家,也有為了孩子爭奪撫養權的媽媽和中學就開始發起衛生巾捐助計畫的職場新人。她們的年齡、地域、學歷和人生經歷都各不相同,但她們感受到的女性命運,在生命中爆發的女性力量卻又相似。
以下是她們的故事和講述。

宋玉蘭
👉
2019年、2023年,我們做了兩期「跟著卡車行中國」,同事們從多個省份出發跟卡車司機同行,其間訪談過的卡車司機不少於五十位,山東濰坊的宋玉蘭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卡車司機。2019年,交通部授予「全國最美貨車司機」的名單當中,宋玉蘭也是唯一的女司機。
關於這份職業,她是這樣講述的:
我不到20歲去學掛車,一批學員40個,我是唯一一個女的。
一般都說女的開不好車,從學車那會兒起,我就是那個「參照系」。
常聽教練說學員,你這車開得,還不如小宋呢。小宋我雖然是個女的,但在那40個學員裏,我永遠是排前面的。比如最難的倒車入庫,並排兩個車位,規定要在三四把內從一個挪到另一個。那會兒掛車不像現在好開,老東風老解放的方向盤死沈死沈的,我那時候才八九十斤,胳膊細得跟竹竿兒似的,就是這樣,倒車入庫我還是練得比大多數學員都快。
後來我買了車,自己當了老板,僱用替班兒駕駛員,都是男的。有些男的一上車看到我是個女的,第一句話就是,呀,這麽大長的車,你能開得好嗎。不講衛生的,有非份之想的,多了去了。所以碰到好師傅,我就額外記著。有位姓劉的師傅,現在已經退休了,大家都叫他大老劉。我雇他當替班兒的時候,年紀還輕,經驗也不夠,但他一見到我,就喊我「宋老板」,
不是「宋師傅」,不是「妹妹」,而是宋老板。
我就記住他了。大老劉開車技術那是沒得說,他教給我兩個保命技巧,一個是遇到長下坡時剎車不能踩死,二是遇到前方有避險帶提示時,要試試剎車,一旦踩下去剎車有點綿,避險帶就是保命的。這是我體會到沒有男女之別,只有經驗多寡的時刻,我印象很深。
我常年在外跑車,女兒從小跟外公外婆長大,她小時候經常說,媽媽,別的小朋友都是媽媽來接放學,你怎麽從來不來。現在女兒長大了也懂事了,這是我最欣慰的。今天剛從新疆拉了煤回來,歇兩天,第三天繼續出發!(記錄:駁靜)

糖匪
科幻作家
2023年4月,科幻作家糖匪出版了一本新的科幻小說集【後來的人類】,我去找她聊了一次很長的天。這幾年,糖匪寫的科幻越來越貼近現實,討論在技術包圍下,普通人的心靈如何發生微妙的變化與沖撞。女性常常是她故事的主角,家庭主婦、美妝主播,她們在「後人類」時代的日常生活中努力追求有靈魂的自我。在我們的聊天中,我發現糖匪並不愛談自己的女性科幻作家身份,而是面向現實,提起一些引起她憤懣或同情的女性困境。以下是她的思考:
今天,身為女性最先要學習的事,也許就是不害怕讓別人失望。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樣子,並且無拘無束地去實作它。
我的確比較幸運,一路野生野長,沒有想過女孩子應該怎樣怎樣。一個經驗是只要讓對方失望得足夠快,你和他們就都會忘記這件事。從來,從來沒有一個人問過我,你是女性,你為什麽寫科幻。可能我身上某些東西已經讓人意識到這是蠢問題,最好別把它說出口。
以上所說都有一個前提。但是很長時間以來,和絕大部份幸運的人一樣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份幸運不具備普遍性。大概在2017年左右,陸陸續續看到衛生巾貧困問題,農村女性不能擁有平等土地繼承權這樣的社會報道時,我內心極度震驚和自責。無論對這樣的現實,還是對哪些可能更糟的未來,我都是負有責任的。必須做點什麽。這個想法不僅促使我寫下貼地飛行的女性主義科幻,更是激發了我身上的女性氣質。是的,我要成為她們的姐妹。
女性生存和發展所要克服的阻礙讓我們變得更強大。當變化的颶風襲來,當我們恢復自身主體性後,就會變成我們的優勢和特長。共情,變通,包容,堅韌,勇氣,犧牲,富有創造性地開辟出新的解決問題的路 徑 ,不是制造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創造出復雜多元的伴侶關係。這才是整個人類能繼續繁衍生存下來的道路。
女性不是男性之外的第二性,也不是男性的對立面,女性是人類未來的第一作者。 科技的發展,讓體能優勢迅速貶值。無數種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裏,將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和人交融的賽博格也許真的會從女性中誕生,徹底打破男和女矽基和碳基邊界,進入更廣闊的天地。
總之,長大這件事真的太好了。 這麽多年過去,我終於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一個很酷的婦女。
劉媛媛
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動物飼養繁育部副部長
今年一月第一期,周刊推出了一本【重新發現動物園】的封面,講述了近幾年發生在動物園的變化,以及對人們形成的吸重力。劉媛媛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采訪物件。她目前是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動物飼養繁育部副部長。在紅山工作的11年中,她擔任過動物譜系管理員,做過一線的飼養員,養過大熊貓、犀鳥、丹頂鶴、猩猩、黑猩猩、合趾猿、狨猴、虎、豹、熊、歐亞猞猁、長頸鹿等動物。 她是紅山動物園第一位養猛獸的女性飼養員,她的講述也是從這裏開始的:
為什麽曾經動物園沒有什麽養猛獸的女性呢?以前猛獸籠舍的閘門,有個進行配重的石墩子一樣的東西,非常沈重,女性很難弄得動。從2018年開始,紅山進行了一系列場館的建設和改造。我在2019年進入新建設完成的中國貓科館開始接觸豹子這類猛獸時,這裏的籠舍已經變為了輕便的推拉門。所以說科技改變生活, 當動物園的設施得到改善後,它就不會去對飼養員的性別有所挑選。 今天在紅山動物園,一線飼養員男女的比例也接近平衡。
因此我認為 作為飼養員所需要的良好的素質和性別沒有關系 。男性也可以很細心地去觀察動物的情況,給它們以無微不至地關懷。好比人工育幼這件事情,個別動物幼崽由於某些原因被自己的母親棄養,需要人工來進行哺育。如果你是一位有過生育經驗的女性,你當然對那種夜晚要頻繁起床、不斷要根據幼崽反饋來調整餵養內容的過程非常熟悉,但我們這裏也有非常年輕的「奶爸」,盡管自己還沒有養育孩子的經歷,卻能全身心地投入去照顧動物,在餵養最初的階段甚至24小時守候在幼崽身邊,滿足它們可能間隔一兩小時就要喝奶的需求。
養動物,主要是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比如貓科動物館有一只豹子有著雙側對稱性脫毛的狀況,之前也接受過獸醫的治療,但效果改善不明顯。我給它調整了食譜,還透過一些「豐容」的做法減少它在環境中感到的壓力,它的毛真的慢慢變得油光水滑起來。養動物最開心的時刻就來自於它們給你的正反饋。好比一筐一筐往籠舍裏擡墊料,弄得自己灰頭土臉的,但是當看到動物在上面打起了滾兒,你心裏是由衷地快樂。還有我曾經費很大勁給老虎做過一個「不倒翁」,相當於是一個提供對抗性的大玩具,老虎真的花了很時間在玩它,那也讓你感到很值得。我的兒子今年5歲,也時不時會來逛動物園,他會覺得我能把這些動物照料好是件很酷的事情。(記錄:丘濂)
陳小燕
👉
開在紹興西小路河岸的河埠頭飯店做的是傳統紹興菜,我去采訪這家店那幾天,趕上冰冷凍雨天,回想起來,熗蟹配上甜滋滋的熱老酒,再沈悶的心緒也都化解了。
老板陳小燕,大家都叫她小燕姐,是位講話溫柔做事卻很堅定的女士。2009年開起河埠頭飯店之前,她其實已經開過三次餐廳,三次都失敗了。不服輸。後來跟陶軍師傅兩個人做起這個小飯館,風裏雨裏,著過火,被偷過,走過疫情,去年又有一輪關店潮,反而就這樣堅持下來了。 小飯館的女老板是什麽樣的體驗,小燕姐是這樣講的:
小飯館嘛,食材新鮮最要緊。開店這麽多年,買菜都是我去。別的餐館可能一天去一次菜市場,我是寧可辛苦一點,中午晚上兩餐的食材是分兩次去買的。市場有對專門賣野生魚蝦的夫妻,人家也幹了二十年了,老板大家都叫他「大嘴巴」。我開始買菜後,慢慢知道大嘴巴是每天淩晨三點去諸暨鄉下,一個點一個點地收野生的魚啊蝦啊,比市場上一般的東西都要貴,但東西當然好。我摸透時行情,也跟其他人一樣,每天到點就在路邊等。
一起等的,有時候五六個人,有時候七八個人,都是我這樣的小飯館老板,都是男的。我麽個子小小的,反正就跟他們站在一起等。等的時候不覺得什麽,大嘴巴收魚的車一到,大家一哄而上,那時候就覺得我一個女的不太行了。大家都是「咚」地跳到車上,就去搶好東西了。那我哪裏搶得過那些男人啊。
就這樣搶了幾年,有時候搶得到,有時空手而歸。後來大嘴巴看我一個女的,總是搶不到,就提前給我留點好貨,現在菜市場上的人會這講的,小燕嘛,大嘴巴都給他留好了。
女老板也有優勢,比方遇到客人不滿意的時候。對待客人嘛是這樣的,有時候即便不是我們的錯,也不能吵架。我是看到有些飯館的男老板,脾氣差,遇到不講理的客人他是忍不住的。我麽碰到這類情況,溫和地說兩句,事態就平息了,和和氣氣做生意嘛。 控制自己的情緒,能跟客人好好溝通,這就是做生意的一種能力,這種時候比力氣大,比嗓門大,是沒用的。
最近餐飲不好做,我們店的生意倒還算穩定。聽說日本有些很小的店也能做成百年老店,我跟陶軍兩個覺得能這樣守著一家小飯館做下去,也是很好的事。(記錄:駁靜)

彭婉芊
👉
2021年,一群四川高中生自發組織了一個名為「拾她」的學生社團,幫助偏遠山區女性解決「月經貧困」問題引起了我們的關註。我當時采訪了「拾她」其中一位創始人,18歲的彭婉芊,她當時剛開始在美國大學一年級的生活。而如今,她已經21歲,大三即將畢業,即將進入職場。 以下是她的口述:
做公益三年多的時間裏,我在幫助女性的同時,自己也對女性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透過做公益,我接觸到了許多女性,有農村喪夫的年輕母親,有女性企業家、創業者,以及背景不同但和自己一樣的年輕女性。過去,在我眼中,男女的定義,像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厚墻,好像女性必須安靜優雅,男性一定動如脫兔。但隨著視線變得越來越遼闊,我越來越覺得,男女的區別,越像是河流匯海的分界線般越來越模糊。其實,男性也可以有「女性」氣質,女性也可以有「男性」氣質。
最近,我在找工作,我看上了一家錄取率極低,且女性員工不到10%的公司。因為喜歡這裏的工作內容決定試一試,盡管有一些不熟的男同學「善意」地提醒我,這裏的工作環境和文化可能會不太適合女性。但我並沒聽從他們的建議,在經過了公司10多個男領導的面試後,最終成功拿到了這家公司的錄用通知。
經歷過這次面試,我感到,當女性有處於一個女性占少數的強競爭環境中,就會有人跑來打著關心的理由告訴我們,要趁早放棄。如果聽從他們的建議,這些環境中的女性,最終會越來越少。所以當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後,便學會了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女性力量可以是很多,但對於最近的我來說, 女性力量是勇於挑戰,忠於自我,不因他人所言束縛自己。 (記錄:印柏同)

朱雯琪
👉
2022年3月中旬,28歲的朱雯琪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釋出了一段畢業視訊,宣布「以牛津年級第一的成績,從數學建模系畢業了」,卻引來質疑,成為陌生網友口中學歷造假的「學術媛」。隨後,她迎接挑戰,線上解題,用多種方式證明了自己的身份。這件事之後,曾經長期身處大學數學系和金融行業等男性主導環境裏的雯琪開始更多思考女性身份問題。 以下是她的講述:
研究生畢業分享這件小事引發的懷疑和攻擊,讓我產生了很大的集體共存感。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人在社會的第一共識標簽,可能就是「性別」。
隨著學歷被證實,很多人不再質疑我的數學博士身份,但轉而開始討論我微博上的風格,說我會在學術圈「社死」。我又開始面對一個如此尖刻的問題:你的風格、形象、生活像哪個圈子的人?
我想,這件事之所以引起了這麽多女性的共鳴,是因為大家看完都會不約而同發出那個疑問:如果ta是男性,還需要自證學歷嗎? 即使需要自證學歷,ta還需要被批評風格嗎?
與男性相比,女性似乎帶著天生的不被信任感,這迫使她們在向上的道路上總需要自證:證明自己的優秀,證明自己優秀的合理性,甚至證明自己優秀的權利。1997年,史丹佛大學神經生物系教授Ben Barres公示選擇變性。在變性前,Ben曾想申請麻省理工,卻被老師無情打擊:「MIT是不會錄取女生的,沒有女生學理工科。」當Ben解出一道難度極大的數學題,教授卻意味深長地問:「是不是你的男友幫你做的?」當Ben變性之後,學術圈立刻變得友好又寬容。他說:「變性後,我第一次感受到說話時可以不被男人打斷、不被質疑。」
我所知道的是,牛津今年部份系招生都開始執行無性別制了。送出簡歷的時候,系統會過濾掉任何種族,性別相關的資訊。這或許是一個值得看見的方向。
我也在這個事件中,感受到了女性共同體的力量。當我把這個事件講給我的女導師聽的時候,我的女導師直接問我是否有談到woman in mathematics(數學界的女性),她指出那些hater(攻擊者)可能是仇女,是sexists(性別歧視者)。她像母親和閨蜜一樣地告訴我千萬不要自責,我並沒有做錯。 這是一種超越了語言、國籍和年齡的共鳴,只因為我和她都是女性,都是數學裏的女性。這就是一種共識,就像女性的一種秘語。
這件事發生後,我想過退網,但是信念感和親朋好友以及陌生人的理解、支持和愛讓我繼續下去。現在,我依然在社交媒體上表達,討論女性議題,參加與女性相關的公益活動,我願意成為更好的自己,為消除不平等做出一點貢獻。希望下一次,在世界的另外一個角落,一個姑娘分享自己的成就時,那個想罵她「學術媛」的人,會想起我做的那道數學題。(記錄:李吉喆)

魏圓圓
👉
2022年9月,我們報道了魏圓圓爭奪兒子撫養權的經歷。2019年初,法院對魏圓圓與男方崔某關於非婚生子聰聰(化名)的撫養權糾紛做出一審判決,未滿兩周歲的孩子由男方撫養,魏圓圓每月支付撫養費直至孩子18歲成人。
這個判決在當年轟動一時,孤身一人的「北漂」媽媽與一個優越的北京家庭之間的「戰爭」就此打響。魏圓圓既要拼命保住工作,證明自己的經濟實力,又要為了守住兒子,忍受成為「限高」失信人後的諸多不便,還有與男方搶孩子時的驚心動魄,以及準備帶孩子「跑路」的決心……最終在三年多之後,法院最終做出了判決,聰聰改由魏圓圓來撫養。
我們的報道就發生在這個節點上。它既具有公共性的法律意義,從個人角度講,魏圓圓的率直和坦誠、原生家庭與情感需求、雞娃的決心和對兒子的期許,同樣構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女性故事。兩年後,我們回訪了魏圓圓,希望她和孩子一切安好。 以下是她的敘述:
我第一次打撫養權官司的時候,因為太累,肩頸不好。有一次去一個按摩店裏推拿,正好有個熱心網友給我算生辰八字出結果了。她拿著我和聰聰還有崔某的八字,一大早上跑去了很遠的山裏,找一個據說很靈的老師算。她告訴我,聰聰跟他爸爸的緣分更深,跟我緣分淺。 我當時就崩潰了,趴在按摩床上哭了全程。
當時非常地脆弱。一個年輕的未婚女性,想撫養自己的孩子,在沒上法院前,遭到了男方各種語言威脅,比如給你很少的撫養費,撫養時不提供任何的幫助,跟你打官司爭到底。上了法院又輸了官司,被迫訴諸輿論,再卷進輿論的漩渦。緊接著二審形勢也不樂觀,那時多少次是向神明伸出求救之手的,結果連老天都不幫你,於是就根本控制不住眼淚,慘哭了一場。結果推拿做完時,我也哭差不多了,與此同時心裏突然升出一股子力量,哪怕我沒有對方有錢,沒有對方有權勢,哪怕法院不站我這邊,哪怕有人詬病我,哪怕連老天都不向著我,我也要爭到底,我也要跟命爭。
這種情節在電影裏叫做「靈魂黑夜」,主人公在陷入最大的絕境時,突然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鼓舞,於是開始奮起。我是做電影行業的,對這種電影敘事結構很了解,但實際自己在遇到困難時,並不能靠這種力量去解決問題的。
兩年前,我最終拿到法院判決,得到撫養權的時候,其實很想從公司辭職,因為不用再證明自己有穩定的收入了嘛。一方面想多陪孩子,想嘗試做點其他的事,另一方面,當時公司從院線電影開始轉向做視訊短劇,我不是很喜歡。但是兩年之間,視訊短劇變得這麽火,從一開始做帳號內的短劇,現在變成了小視訊付費短劇,我過年回老家,縣城裏的姑姑都在看,短劇發展非常快,我的收入也比以前更好了,所以短時間內還是要繼續在這個行業做下去。
去年我拿到了公司「最佳員工」獎,因為做出了爆款短劇。在那時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心態,每當我感受到自己很厲害時,我只覺得自己是個男人,甚至會說出「自己像個男人一樣」這種話。你知道我處在一個基本還是男性站主導權的行業裏,因為業務能力強,甚至被合作方直接叫「哥」,你厲害,別人就不把你當女性看。 其實並不是因為男性天然更強,而是女性總與弱勢掛鉤,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方式來形容自己罷了。 (記錄:吳麗瑋)

熊昱彤
攝影師、【行走三境】作者
熊昱彤是我們長期合作的撰稿人,在三聯公眾號的「視覺」欄目發表了許多讓人印象深刻的攝影圖文。作為一個旅行與文史愛好者,她在人生過半的時候,走出了安穩的上班狀態,開始背著相機勇於探索小眾目的地。她的攝影作品與文字飽含著對自然的敬畏、對人的觀照,以及對歷史和傳統的探究。以下是她的講述:
9年前,我走出了存續近三十年的上班族狀態,重新拿起閑置多年的照相機,並突然發現了自己真正喜歡做並且做得還不錯的事情。
旅行、攝影和寫作為我開啟了一扇窗,這些年,我去過北極、南美、非洲、澳洲、南亞以及中國的西部高原,旅途和創作中的艱辛,在完成之後也是一種幸福的報酬。
攝影是個「力氣活兒」。論體力,女性肯定處於劣勢,一個相機包往往裝著兩個機身和3-4個鏡頭,若再加上無人機和電池,足有10多斤。背著相機包徒步行走和爬升,尤其在西藏、青海這些高海拔地區,走不了幾步就得停下喘粗氣。在荒野中露營,能夠想見到女人要克服比男人多得多的各種不便。2019年秋在珠峰東坡噶瑪溝露營拍攝,整個山谷中,我們的團隊加上藏族馬夫、牦牛工總共十好幾人,只有我一名女性。
但多年的行攝體會,讓我感覺到女性在攝影中,尤其在人文攝影中,也有特殊的「女性力量」。相機和鏡頭本身會帶給人以侵略性,而女性溫和柔韌的性格特質會讓被攝者感覺到被冒犯的程度減低。也許,在男性居多的攝影圈裏,普遍低調、謙和的女攝影師,相對一些自信爆棚、甚至咄咄逼人的男攝影師,更易與人和睦相處。
摩洛哥以「不讓拍」而著稱,所有來摩洛哥「掃街」拍人文的攝影師都因此而頭疼,這裏的人對被拍照有一種強烈的反感甚至懼怕。但那個在馬拉喀什的傍晚,在我連連遭到拒絕、連看風景的心情都變得糟糕時,一個正在做活的男裁縫,可能是看到了我端著相機又不敢拍的窘境,主動用英語柔聲說「OK,沒關系」,對著我的鏡頭微笑,瞬時讓我深受感動。
電影裏的印度貧民窟總是充斥著犯罪毒品和恐怖場景。但我在孟買的達哈維貧民窟,並沒有這樣的感受。這裏的人雖然貧窮,卻樂觀友善。一位開小店的穆斯林兄弟,看到我在拍他,也幽默地拿起手機拍我。奇妙的瞬間出現了:我和他同時按下了快門,我的相機抓到了他手機閃光燈發出的星芒。

女性和善細膩的特點,能讓我拍到也許男性同行拿不到的片子。在香港,菲傭們的周末派對是香港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頂級繁華奢侈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閑」的菲傭們如同局外人一般,自在灑脫地享受屬於自己的時光。我走入菲傭的圈子,和她們一起席地而坐,聊家常、分享食物。她們和我講述在雇主家的感受,讓我看家人的照片。看到那些在街頭舉著手機跟家人視訊的菲傭們,讓人心裏不由泛起一絲心酸。入夜,遍地的紙盒、鋪布和席地而坐的膚色黝黑的女人,異鄉漂泊的疲憊孤獨,與燈火輝煌的中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帶著女性特有的敏感和關懷,我拍出了一組有溫度的圖片。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沈洋是我的同事在做女性話題時曾采訪過的一個研究者,她是上海交通大學 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城市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員,性別議題正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公共研究之外,她也經常為我們撰寫文章,將自己遇到的個體經驗置於公共結構中加以審視,她的經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如今女性自我覺醒、得到力量的一種路徑。以下是她的講述:
你問我女性力量和女性束縛,我更多時候還是會感覺到女性的束縛。我從小是獨生女,家裏的女性同輩當中,女性整體讀書也比男性好,所以小時候沒什麽重男輕女的感覺。
但到了高三,我英語好,想報考上海外國語大學。當時上外在我們中學有三個提前招生的名額,按排名我是夠資格的,結果學校推了三個人,沒有我。我就去問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就說,你是男生的話,還有希望加一個名額。言外之意,還是優先考慮男生。後來我特地坐了三個小時的公交車,想跑去上外的招生辦爭取一個名額,結果我跑錯校區了,沒找到,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後來我考上了復旦,讀的文科,有一次系主任給我們上專業必修課,公開說,招研究生喜歡招男生,覺得女生後勁不足。我知道不少理科老師會說女生後勁不足,結果文科也一樣。當時我們系裏的教授,也是男性主導,聽說那位系主任當時已經結了三次婚,第三次就是跟自己的女學生。當時大家不會用性別歧視這種詞來概括這事,但我印象很深,感覺很諷刺。
後來我出國讀博士,研究的是性別平等問題,在被訪者身上碰到比如說家庭內的性別不平等分工,就太常見了。所以無論從我自身的經歷,還是我的研究來說,我感覺女性還是受到束縛比較多。
不過我讀博的時候,周圍很多誌同道合的朋友。我記得有一次跟一個女性朋友去看【瘋狂的麥克斯3】,裏面的女主角槍法很準,有一個鏡頭,女主角幹脆利落地把子彈打出去,打得比男性好,那一刻我跟我旁邊的朋友突然對視了一下,會心一笑。那種感受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就是隨著那尖銳的「砰」以及我們的對視,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女性連線帶來的力量感。
我現在在跟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的蔣萊老師寫一本書,內容跟中國女性面對的生育問題有關,比如生還是不生孩子,生幾個孩子等等。寫的時候,我們也在挖掘自己的生命歷程,包括生育決策,跟母親的代際關系,相當於在寫書的過程中,我們對自己、對彼此、對受訪物件都更了解了,連線變得很深,這種感覺也蠻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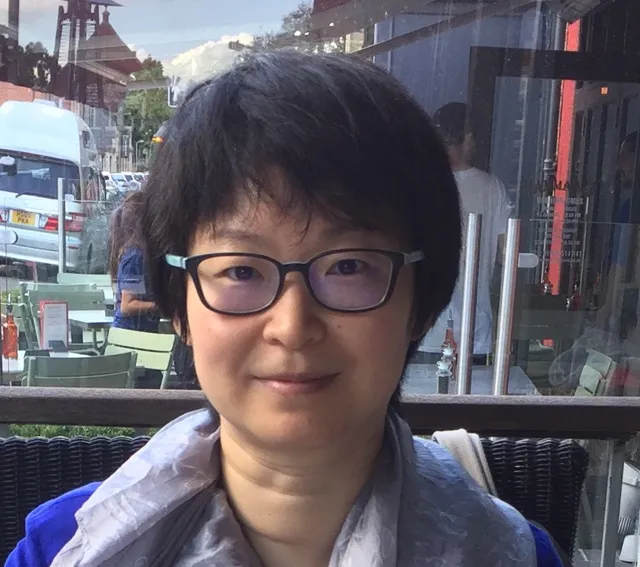
孫欣
多倫多大學分子遺傳學博士、牛津大學生理解剖與遺傳系博士後
孫欣原本是給雜誌生活圓桌欄目寫稿的作者,那個欄目主要是接收一些展示生活趣味的小文章。後來,她也漸漸給我們寫更多的約稿,題材廣泛,從動漫回憶到書評到社會觀察,但我們一直不知道她是幹什麽的。後來有一次,她有給我們寫了一篇約稿,得到副主編的表揚,「稿子寫得好,而且還是個科學家」,聯想到她在文章裏寫,她還有一個孩子,我們全都大吃一驚。以下是作為一個女科學家,她對自己生活的講述:
在博士畢業典禮的那天,我坐在會堂裏,穿著黑袍子,等待校長叫到自己的名字。在無聊中,我開始數今天來參加多倫多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典禮的女生占多少比例。數數的結果令我驚奇:碩士中的女生占將近七成,博士至少一半。這麽多女生進入研究生院並成功拿到學位,是什麽在激勵著她們呢?聯想到我自己,好象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感召。 當社會的束縛和偏見減弱了,生活中的選擇變多了,女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還有她們勤勉、細致、耐心、善於交流合作的特質,自然而然引領她們進入科學研究的大門,探索廣闊的宏觀和微觀世界。
我喜歡研究動物,所以我的博士研究方向選擇了發育生物學,一直到現在。發育生物學,我認為動物發育是個神奇的過程——一顆粒球在合適的環境中,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最後竟然能生成一整個動物!更為神奇的是,我們人類也是透過這樣一個發育過程形成的。我們有足夠的智慧創造出「發育生物學」這個概念,研究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研究物件包括我們自己,包括我們日夜跳動維持生命的心臟,還有用來記憶和思考的大腦。在普通人的認知裏,離開母體哇哇大哭的新生兒是生命的起點。但是在發育生物學的視野中,新生兒的起點是最初的那個受精卵,而卵子在女性還是胎兒的時候已經確定了。
生命起始和延續的秘密一直由女性的身體傳遞,如今女性大量進入科學領域,用她們聰明的頭腦和豐富的生活經驗解答生命之謎。女性現在是發育生物學的主導力量,我讀博士的實驗室,做博後的實驗室,主導力量都是女性。我工作的這一層樓,七位實驗室負責人中有四位是女性,近五年畢業的九名博士生中有六名是女生。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女性就承擔著孕育生命和撫養生命的工作,現在,女性正在成為生命研究者的主體。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編輯:王海燕 / 排版、 稽核:小風
招聘|實習生、撰稿人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
本文為原創內容,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轉載請聯系後台。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