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文|湯寶
以下內容涉及劇透,請謹慎閱讀
以前文化界有兩個膾炙人口的金句。一句是「生活在別處」(昆德拉語),另一句叫「他人就是地獄」(薩特語)。後面網路上廣為流傳的「生活不僅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致賤人」之類的說法,無非是原句更通俗易懂的版本。 然而似乎並沒有人指出,這兩個金句是相互矛盾的,把「別處」想得太好,或者把「他人」想得太壞,恐怕都是想得太簡單了。
之所以會想起這茬,是因為看了HBO的高分熱劇【東京罪惡】。此劇剛剛播完第二季,口碑頗佳(在著名影評網站爛番茄的新鮮度高達92%,向來苛刻的豆瓣也有8.2,IMDb平台在開播以來,評分持續走高,第十集直接飆升到9.3分),後續很可能還會有第三、第四季。全劇基於同名非虛構作品改編,全稱【東京罪惡:一個美國記者在日本的警方報道實錄】。作者傑克·阿德爾史坦是日本大報【讀賣新聞】的首位「外國人」記者,且專門負責犯罪報道。
【東京罪惡】劇照
傑克一幹就是十二年,每周工作80小時,揭露了東京花花世界背後盤根錯節的陰暗鏈條,尤其是與黑幫相關的各種可怕罪行——這些事情主流社會的日本民眾其實也都是不太了解的。有時候非得有一個外來者捅破窗戶紙、快刀斬亂麻。傑克的報道終於引來黑道登門威脅,而這正是他寫下此書的緣由。 用文字打敗刀槍,用熾熱的雙眼照亮渾濁的世道,這種故事從古到今,永遠都激動人心。
電視劇中除了主角傑克(安塞爾·艾爾高特 飾)保留真實姓名以外,其他大多都用了化名,比如【讀賣新聞】變成了【明調新聞】,臭名昭著的黑幫「山口組」成了「戶澤組」,黑幫老大、相關警察、記者同僚的名字當然也都改過。雖然劇組的官方口徑,這是為了保證藝術創作的靈活,但觀眾能夠感受到,其實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真相過於敏感。全劇的調子可以說相當寫實,「東京」並沒有淪為西方視角下的東方奇觀,而「罪惡」的部份也沒有輕易陷入黑幫片的窠臼,而是始終保持了生活的沈重與切膚之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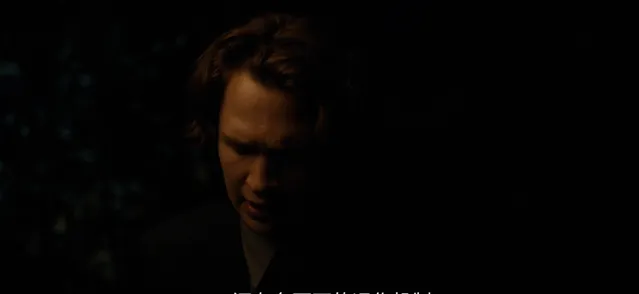
為什麽觀眾容易與傑克這個雙重意義上的局外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東方人)共情,用托爾斯泰的話來說就是:現代大都市的生活總是相似的——尤其是不幸的部份。在全劇開頭,我們跟隨傑克遊走於東京的大街小巷,但更令我們熟悉的是他手裏始終拿著日文教材,哪怕在面館裏也要攤開來爭分奪秒地學習、學習、再學習,完全是一副做題家、考編狂人的風範。
東京居,大不易。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開始慢慢浮上觀眾心頭,到底是什麽讓一個老家在美國密蘇裏州的白人青年,不遠萬裏來考日本的記者?
正是這個疑惑,讓我想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日本對於傑克是一個「別處」。他來到日本,最主要恐怕並非迷戀日本文化,而是要盡可能地遠離家鄉,遠離父親和熟悉的生活,就像王家衛電得影【春光乍泄】裏面,黎耀輝與何寶榮之所以非要去阿根廷,只因那是離香港最遠的地方。

當然,真實的東京總是超出傑克的想象。他很快就碰到了「他人即地獄」的一面。他高大的身影在日本狹小的辦公室裏,總是顯得如此笨拙、莽撞、格格不入。而除了物理空間的限制以外,更有無數隱形規則的束縛。比如按報社的要求,一篇報道有非常嚴格的格式要求,絲毫不得僭越,而在這份格式一般只交代時間、地點、人物等基本資訊,但偏偏沒有讀者最感興趣、記者也最應該感興趣的部份,那就是「為什麽」。

明調新聞官方的說法是「有空間剩余的話可以最後再寫寫為什麽」、「但是通常不會有這種剩余」。 報社的諱莫如深,恰好反映了日本復雜的社會結構:在日本,黑社會是合法的,因此與警察之間的關系就異常曖昧,不乏像宮本(伊藤英明 飾)那樣油滑的黑警,明目張膽地給黑社會控制的夜總會拉客。而即使像片桐(渡邊謙 飾)這樣硬派的正義警察,對於黑幫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求表面的平靜和平衡,別光天化日地打打殺殺就行,夜晚如何暗流洶湧就顧不上了。

而跑社會犯罪這條線的記者,訊息完全來自於警察的放料,自然得巴結好關系。傑克的第一篇報道寫一個暴屍街頭的案子,此人身上插著刀,顯然是遭到殺害,但傑克的主管卻大罵了他一頓,原因是他在報道裏使用了「受害者」一詞,沒有按警方的通告寫。後面宮本就很直白地告訴傑克,「東京是沒有兇殺案的」——除非有人親眼看到兇殺的過程,否則永遠只有死因不明的屍體。而如果記者用了「受害者」這樣的字眼,警察又不能盡快破案的話,面子上就會很難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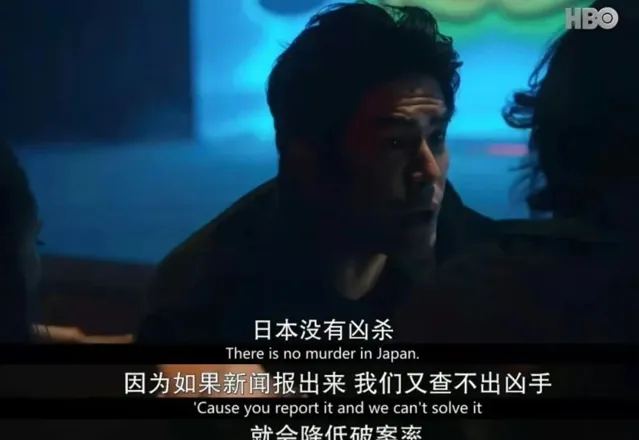
東京在近年很多「城市安全指數」裏名列前茅,甚至很多時候就排第一,不知道有沒有前面提到的這層關系。【東京罪惡】的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末,想必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但一個人在大城市裏走投無路,並不一定和黑幫有關,而且黑幫也有無數種合法的手段來逼死無辜的人。第一季的主線就是講戶澤組開辦合法的高利貸公司,然後透過不斷羞辱借款人,令其精神崩潰自殺,從而收取高額保險金。
劇中一位自殺的中年人遺孀對前來調查的傑克說,先夫自殺,不是單純因為還不上錢,而是因為不想再羞恥地活著。 在一個規矩越多的地方,自然就會越多觸犯規矩的風險,也自然會產生更多的羞恥。 【東京罪惡】向觀眾展示了,在這種超級摩登的大都市裏,羞恥的罪惡遠遠大於罪惡的羞恥。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適應這種冷酷無情、卷到極致的叢林法則。不僅普通人疲於奔命,甚至連黑幫分子都適應不了——如果他們不能比自己的同類更狠、更不知羞恥的話。

此劇雖以傑克的故事為主線,但傑克只是主角之一,記者的調查也只是故事線之一。另外兩大主角是夜總會的外國陪酒小姐莎曼莎(瑞秋·凱勒 飾)和黑幫小子佐藤(笠松將 飾)。莎曼莎和傑克一樣,也是為了逃避過去而背井離鄉。很顯然在東京夜總會當陪酒女,並不能說是什麽好日子,但是她的人生,就像她喜歡騎的摩托車一樣,只能往前開:她只能在陪酒女到女老板(「媽媽桑」)這條路上奔馳下去,而不可能再倒退回過去,當一個虔誠的傳教士。

莎曼莎的同僚(後面一部份變成了她的手下)是一幫與她命運大同小異的外國女青年,她們為何橫跨萬裏落腳東京,原因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她們都絕對不會回去,可以說到了寧死不回的地步。有時候真的很難說清,東京究竟是給了她們第二次機會,還是用它的繁華艷麗、紙醉金迷,斷了她們回家的路。
陪酒這行,雖然出賣色相,到底還是很能賺些錢的,這些錢就像流水,來得快去得更快,到頭來什麽也抓不住,比如莎曼莎最要好的閨蜜就把全副身家都浪費在牛郎店裏。東京是一場大夢,一場宿醉,本來總要醒的,可是這夢太美,這醉太深,終於有一天醒不過來了——這正是莎曼莎很多姐妹的結局:客死異鄉,無人問津。

而黑道小子佐藤的情況,恰好和傑克與莎曼莎相反,他從小被趕出家庭、流落街頭,為了生計而不得不加入黑道「千源會」。 他渴望家庭,卻有家難回,黑幫成了家庭的替代品,黑老大石田仁誌(菅田俊 飾)成了他的替代父親。 與其說佐藤的故事展現了一個天真善良的年輕人如何一步步變得殺伐果斷,倒不如說他為黑幫故事註入了一個人性化的視角,讓觀眾不再把他們簡單地看成怪物和毒瘤。 不,他們不是外來的害蟲,而是這種城市生活本身結出的果實。
正如石田老大對警察說的:沒有黑道,日本會崩潰。這一點在佐藤身上再明顯不過。如果沒有千源會,那他的結局無非是兩個,要麽暴屍街頭,要麽變成一個孤狼式的犯罪分子。有一個組織把他管起來,不論對他自己,還是對社會整體而言,其實都是好事。在城市豐饒的海平面以下,其實有無數像佐藤那樣陽光難以觸及的浮遊生物,但他們也是生態系的一部份。
黑幫其實是給走投無路的年輕人一條最後的出路,雖然他們總是遊走在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好像總是與暴力脫不開幹系,但其實那也是一份「工作」,同樣朝九晚五,很少有什麽快意恩仇。
傑克、莎曼莎和佐藤,三個人由於復雜的情感和案件糾葛給綁在了一起,構成了一個奇特的三人組。觀眾看著看著,會突然發現他們看似迥異的生活,其實多麽相似——他們都受制於同一套「東京規矩」。警察、記者和黑道,都一天到晚穿著西裝(當然陪酒小姐穿的是另外的制服),都有自己嚴格的規則和潛規則。黑道搞得像個公司,而報社卻又像一個幫會。 說到底,對於這座大城市來說,所有人都是打工人,所有人都身不由己。
我個人對傑克更有共鳴,因為我也當過短暫的社會記者。我跑的當然不是什麽大案子,卻也讓我目睹了不少人間的悲歡離合——應該說主要是悲。由於我供職的也是一家報紙,很多新聞其實並沒有後續。比如我跑的第一個案子是一個農民工去黑診所註射不明液體後進了急救室,最後我並不知道他有沒有活下來,黑診所的人又下場如何。我甚至不明白為什麽要報道這件事,也許只是需要填一個很小的天窗而已。
新聞就是這樣的,它很容易就被人遺忘了。 歐登說「文學是永遠新鮮的新聞」,其實就是在說新聞多麽容易過期。片中傑克和幾個小夥伴,登了一點豆腐幹大小的小文章,都要下館子好好慶祝一番,好像世界真的會傾聽,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那種喜悅非記者不能體會。但其實他們自己也知道,這種報道的影響力很微小。想要用報紙新聞來扳倒黑幫,簡直就是不自量力。不過傑克的頂頭上司丸山女士(菊地凜子 飾)一直教導他要從寫好小文章做起,從寫清楚每個受害人的名字寫起—— 正義沒法一蹴而就,只能水滴石穿。

【東京罪惡】開篇第一集專門請了大導演麥可·曼來拍,我這回還專門倒回去重新看了一下。最令我感慨的倒並不是導演技法如何高超,而是在知道結局的情況下,重看每個角色的相遇。一切都顯得多麽偶然,誰也不知道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會成為此生摯愛,一個流盼中的陌生人,會在接下來的日子生死與共。這是時間的魔法,也是城市的魔法。 東京這樣的大都市裏,永遠充滿了喧嘩與騷動、機遇與誘惑,無限的可能性像霓虹一樣閃爍。說到底,你不能怪城市罪惡,而是得小心選擇。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排版:布雷克 / 稽核:楊逸
招聘|實習生、撰稿人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
本文為原創內容,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未經授權,嚴禁復制、轉載、篡改或再釋出。
大家都在看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