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士英

安史之亂爆發後,馬嵬之變、靈武即位等事,當事雙方背後都有復雜意圖和手段,最終,唐玄宗默許唐肅宗即位的同時,也為自己保留了極大權力,並任命永王李璘等諸王封建各地,還在唐肅宗身邊安插自己的宰相,因此,唐肅宗急於攻陷兩京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白衣宰相李泌規劃的最合理的平叛之策被束之高閣。最終,唐肅宗成功地逼唐玄宗放棄權力,唐玄宗最終可能死於非命。
請輸入標題 bcdef
本文歡迎轉載。
唐肅宗時期最大的政治當為平叛,這既是唐肅宗靈武即位重建中央政府的理由,也是其政治權力與政治地位得以確立的前提條件。
如前所述,唐肅宗即位伊始,就打出平叛的旗幟。毋庸置疑,平叛是此時唐肅宗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
唐朝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即唐玄宗、唐肅宗各自掌權之局),對肅宗朝政治產生了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唐肅宗的整個平叛過程,處處打著這一政治格局的烙印。
其中,又以處理永王璘事件和確定收復長安、洛陽為首要平叛目標最為顯著。
永王是唐玄宗父子角力的棋子
永王璘是奉唐玄宗詔令(【命三王制】)擔任四鎮(山南東、江南西、嶺南、黔中)節度等諸使、江陵郡大都督的。
他於天寶十五載(756年)九月赴任江陵。此時唐肅宗即位已兩個月,並已獲唐玄宗正式承認。
但是,對永王璘奉命出鎮江陵一事,除見隨唐玄宗入蜀的高適有過不同意見[1]外,並未見有人感到不妥,倒是不少人對此寄予了厚望,李白【永王東巡歌】就大致反映了這一趣向[2],現錄第一、第五、第十首如下[3]: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
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為雁鶩池。
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
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從前引【命三王制】的內容來看,永王璘出鎮後招募士將、補署官吏、積聚江淮財賦等[4],並不屬擅權妄為,均符合玄宗詔制的授權規定。

李白卷入政治旋渦
所以,時任廬陵郡司馬的崔祐甫拒絕永王璘厚禮相邀,「人聞其事,為之惴慄」[5]。這說明永王璘能號令江淮,正在於他秉承了唐玄宗的旨意。故而當時有「永王以天人授鉞」[6]的說法。
應該引起註意的是,在唐玄宗為唐肅宗行冊命後,還於至德元載(756年)八月二十一日頒布了由賈至起草的【停潁王等節度誥】[7]。 誥,正是太上皇處置政事的公文形式。 其誥曰:
潁王、永王、豐王等,朕之諸子,早承訓誨……頃之委任,鹹緝方隅。今者皇帝即位,親統師旅,兵權大略,宜有統承。庶若網在綱,惟精惟一。潁王以下節度使,並停。其諸道先有節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並取皇帝處分。李峴未到江陵,永王且莫離使,待交付兵馬了,永王、豐王並赴皇帝行在。
有學者對此誥的真實性表示懷疑。[8]其實,在筆者看來,此誥與【令肅宗即位詔】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確保皇帝在平叛之中的軍事指揮權。誥書中停諸王所領節度使,由副使知事,聽從皇帝處分就是此意。
不過,其中對諸王的安置又耐人尋味。誥書雖然明確停了潁王以下的節度使職權,但強調永王要等到副使李峴到達江陵交割軍務後才可離職。
事實上,李峴根本沒有前往江陵履行職責,他以有病為由直接由長沙奔赴行在,唐肅宗又將他改任為扶風太守[9]。
所以說, 這一誥書並沒有影響永王仍可奉令赴任。 正因如此,唐肅宗下詔令永王「歸覲於蜀」,永王「不從命」[10]。
不過,當年七月已經抵達襄陽的永王到九月方到江陵,短短的一段路竟用了一個多月,實在令人疑惑。也許在唐玄宗的誥命下達後,永王曾對自己是否仍往江陵遲疑過,也未可知。
唐肅宗無奈,只得另制置淮南與淮南西道節度使並江南東道節度使加以防範,意存威懾。畢竟,永王璘節制四鎮、封疆數千裏,又得江淮財賦之用,尚在流亡之中、致力平叛的唐肅宗不能不感到潛在的威脅。
這年年底,永王璘叛亂,至德二載(757年)二月,叛亂即平。史書對永王被殺的細節說法不一,對唐肅宗的態度也有不同的記載。
一說是永王被皇甫侁擒後因中矢而死,「肅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11];一說是皇甫侁在驛舍內將永王秘密處死,唐肅宗說:「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也?」[12]
無論是哪種說法,都說明唐玄宗在蜀仍然具有法統權力,對於永王的處理,唐肅宗不得不有所顧忌。
值得註意的是,永王事件後,永王的家屬是被送往成都而不是交由唐肅宗處理的。在此過程中,褫奪永王的爵位也是根據太上皇釋出的誥命執行的。據【降永王璘庶人詔】:
朕乘輿南幸,遵古公避狄之仁;皇帝受命北征,興少康復夏之績,猶以藩翰所寄,非親莫可。永王璘,謂能堪事,令鎮江陵;庶其克保維城,有裨王室;而乃棄分符之任,專用鉞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亂。違君父之命,既自貽殃;走蠻貊之邦,欲何逃罪!據其兇悖,理合誅夷。尚以骨肉之間,有所未忍;皇帝誠深孝友,表請哀矜。……可悉除爵土,降為庶人。仍於房陵郡安置,所由郡縣,勿許東西。 [13]
根據詔書的內容,這應該是以太上皇的口吻釋出的。這樣的話,【降永王璘庶人詔】本應作「【降永王璘庶人誥】」。
估計這是唐玄宗在永王打算南竄嶺表時頒下的。據此,永王璘雖被降為庶人,但唐玄宗還無意將他誅殺。皇甫侁未能將永王活著送往成都,不論是否屬於擅殺,都與太上皇的本意不符。
唐肅宗對皇甫侁廢而不用,應含有深意。 若非太上皇仍掌握相當權力,豈能如此? 正如賈二強先生所指出者:永王起兵事件「實際上是安史之亂前期統治集團內部主要是玄宗和肅宗間權力之爭的曲折反映」[14]。
既然是權力鬥爭,則至少說明作為太上皇的唐玄宗仍具有法統權力。
總之,永王事件的確反映出唐肅宗時期中樞政局內的若幹真實內容。唐玄宗「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15],自然給唐肅宗的平叛增加了額外負擔,牽扯了他相當的精力,並直接對唐肅宗的施政方略產生了影響。
唐肅宗為何不用李泌的奇謀
唐肅宗以收復兩京為其平叛的中心任務,正是因為唐玄宗的制誥仍然具有法定效力,這是唐肅宗在平叛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現實政治問題。對唐肅宗來說,也是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
唐肅宗何以把收復兩京當作平叛的中心任務呢?唐玄宗先前所頒【命三王制】,以天下四分,諸子分總節制,李亨被安置在沙塞空虛之地且位於平叛前線。
他若不能先收復兩京,則將對其地位的鞏固大為不利。屆時 若永王璘輩「掃清江漢」,更「救河南」,捷足先登,誰主唐鼎,恐怕另見分曉。
這期間,謀臣李泌根據平叛形勢制定了一個分路出擊,各個擊破,以逸待勞,先取賊巢範陽,再取兩京,最終全殲叛軍的作戰方案。唐肅宗極表欣賞,卻無法依計而行。
尤其在河西、隴右、安西、西域大軍匯集,又得江淮庸調之資的情況下,唐肅宗認為「當乘兵鋒搗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裏,先取範陽,不亦迂乎?」
李泌再三相勸並陳說利害,唐肅宗方吐真言:「朕切於晨昏之戀(胡註:言急於復兩京、迎上皇),不能待此,決矣。」[16]所謂「急於復兩京,迎上皇」,遂不能驅兵千裏攻範陽而後得其成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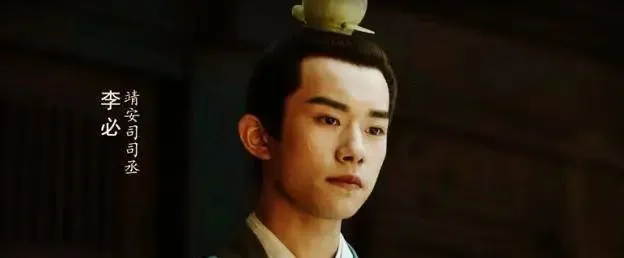
李泌的平叛方略堪稱中國十大對策之一
唐玄宗在為唐肅宗行冊命的詔書中,把自己放棄權力的時間限定在克復西京之後, 這正是我們得以破解 唐 肅宗確定以收復兩京為平叛首要目標的關鍵。
不言而喻,收復兩京,正是唐肅宗在二元政治格局中穩固其既得地位最簡捷的途徑。從郭子儀率兵進攻長安之際向唐肅宗所表「此行不捷,臣必死之」[17]的決心,足可體味出唐肅宗在收復西京一事上急不可待的心情。
長安收復後,唐肅宗言於郭子儀「吾之家國,由卿再造」[18]之「再造」,亦可透露出此中隱衷。關於這一點,王夫之看得很清楚。他說:
「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玄宗且無固誌,永王璘已有瑯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勛,孤處西隅,與天下懸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嫡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統,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 [19]
究其緣由,舍棄二元格局之作祟,宜乎無可言之。
唐肅宗得到長安收復捷報的當天,就「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20],並附表請太上皇歸京。迫不及待地迎還太上皇,與急於收復兩京出於同一理由。
從唐肅宗迎還唐玄宗歸京一事[21],我們可以洞悉二元格局的影響。而此事所反映出的唐玄宗、唐肅宗父子的心態頗值得玩味。
在此事之過程中,筆者以為有幾點應當註意。
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仿徨不能食,欲不歸」,實際上是因為唐肅宗在請歸表中表示「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
唐玄宗心情緊張,應當是擔心「歸京」會打破業已確定的二元格局,引起父子之間實即皇權內部的沖突與更大的政局動蕩。唐肅宗本意當不無對唐玄宗的政治試探,實際是為了讓太上皇早日還京,以便獨掌權柄,結果弄巧成拙。
二、當唐肅宗獲得唐玄宗的誥命「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更是憂懼得不知所措。
唐肅宗應是擔心依然手握權柄的太上皇在劍南形成與肅宗自己遊離的政治中心。事實上,唐玄宗自入蜀後就一直恃劍南自固,發號施令。如果唐玄宗不歸京師,在安史余孽仍盤踞河北的形勢下,極易造成唐朝中央的政治分裂而引發更大的動蕩與危機。起初,父子雙方均感不安者,恐怕即在於此。
三、唐玄宗在接到經由唐肅宗認可、由李泌起草的群臣賀表,雲「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他的態度大變:「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22]
其前後態度迥異,實是見肅宗君臣仍遵循既定的政治格局,既奉上皇,又尊皇帝,即能夠保證他以太上皇身份而不是其他身份還京,從而使父子暫保安處。迎歸太上皇之過程如此一波三折,關鍵在於唐肅宗迎歸的是依然掌握權力的太上皇,而不是可以隨意擺布、可有可無的政治傀儡。
唐玄宗遙控靈武朝局
唐玄宗依然掌握大權並對肅宗朝政治有所影響,這還可以透過唐肅宗時期宰相人選[23]的更換來得到佐證。
唐肅宗即位之初,僅有裴冕一人為同平章事,即宰相。唐玄宗於至德元載(756年)八月為肅宗行冊命時,成都的四位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除崔圓外均被派到唐肅宗身邊。
次年(757年)正月,唐玄宗任命李麟為宰相[24]後,「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25],又將崔圓派往肅宗身邊。
這樣, 唐肅宗身邊五位宰相中有四位是由唐玄宗任命的 ,這雖然說明唐玄宗對唐肅宗即位的承認以及他們有共同的政治目標,但也 反映出唐玄宗對肅宗朝政治的滲透與幹預。
對唐玄宗所委派的這幾位宰相,唐肅宗的使用是有區別的。崔渙到來不久,即被皇帝詔以江淮宣諭選補使[26]打發出去,雖然他遲至至德二載八月才正式罷相,但其實並沒有在肅宗朝中輔政。
對韋見素,因其「常附(楊)國忠,禮遇稍薄」[27],至德二載三月罷相。
唐肅宗對房琯倒一度禮遇,「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琯,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甚至房琯用劉秩等收復長安大敗,「上猶待之如初」[28],不過到至德二載五月仍不免於罷相。
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崔圓、李麟也於同日罷相,至此,「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29]。此後宰相自苗晉卿以下均為唐肅宗所委任。
唐玄宗所置宰相被陸續罷免,情況各有不同,但都是唐肅宗力圖減弱唐玄宗政治影響力的舉措。
賀蘭進明言於唐肅宗 房琯在「南朝」所作所為「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30],就反映出唐玄宗所委任宰相在政治態度上的差異。 唐肅宗因賀蘭進明的一席話疏遠房琯,正反映出他對唐玄宗所任宰相之政治態度心存戒備。
對於這一點,甚至房琯本人都曾看出一些苗頭,他對崔圓的態度即可為證:「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琯意以為圓才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31]
不能不說, 唐肅宗時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使政府官員因政治傾向相異而人事不和,這給平叛戰爭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像賀蘭進明因與房琯有矛盾,在張巡、許遠困守睢陽時,拒不相救,就是擔心房琯暗算他。結果,睢陽在洛陽收復前十幾天被叛軍攻陷,釀成平叛戰爭中的一幕悲劇。
無疑,類似問題的存在大大延緩了唐平叛戰爭的行程,使安史之亂曠日持久。
唐肅宗怎樣弄死老爹
可以這麽說,唐中央政治二元格局由衰竭而解體的過程,就是唐玄宗的權力日益萎縮到喪失的過程。
筆者覺得,這一過程是從唐玄宗重歸京師後開始的。這時,依照【令肅宗即位詔】,唐玄宗的權力失去了法律依據與保障,並且,唐玄宗歸京後處於唐肅宗的嚴密監控下。這一切,都不能逃脫皇權運作的一般法則。
返京之初,唐玄宗尚可在南內興慶宮自由活動,「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上皇多禦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32]。
但是,在唐肅宗的掣肘下,太上皇的權力逐漸被削弱。乾元元年(758年)冬十月唐玄宗幸華清宮,十一月即匆匆而還,如此不盡興,原因無他,「從官嬪禦,多非舊人」[33]也。
而且,唐玄宗從華清宮返回時,唐肅宗還親至灞上相迎,「上自控上皇馬轡百余步,誥止之,乃已」[34]。貌似臣子之孝,實則意存防範,透出太上皇已受監控的玄機。
據載,唐玄宗曾有意以禮改葬楊貴妃,李輔國不從,大臣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35]
李揆借龍武將士置言,而不及李輔國與唐肅宗馬嵬之謀,顯然是提醒皇帝若以禮改葬楊貴妃,必定說明朝廷對馬嵬誅楊一事的態度發生變化,那將對現有政治格局不利。唐肅宗「遂止之」。
太上皇不能如願改葬楊貴妃,反映出他的政治權力已開始淪替。結果,「明皇在南內,耿耿不樂。每自吟(李)太白【傀儡】詩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發與真同。須臾弄(一作舞)罷渾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36]權力失落後的悵惘之態躍然紙上。
即使如此,唐肅宗還是絲毫沒有放松戒備。親信李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37],對興慶官的動靜嚴密監視。他曾對唐肅宗說:「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麗仕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勛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38]
上元元年(760年),唐玄宗在興慶宮「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39]。李輔國乃奏雲:「南內有異謀」[40],這引起了唐肅宗的警覺。
回想天寶五載(746年)李林甫羅織韋堅、柳之獄構陷太子李亨時,就是借口地方軍將皇甫惟明、王忠嗣與東宮交往而大做文章,如今唐玄宗宴請地方軍將,唐肅宗當然難以放心。
於是,在上元元年(760年)七月丁未,發生了李輔國以兵逼迫唐玄宗遷宮之事。
據【通鑒】記載,事情發生前一天,興慶宮中的三百匹廄馬被李輔國借口索去,僅剩十匹,足見遷宮之事不僅有預謀,而且部署周密。
當日清晨,唐玄宗還曾離南內到北內,唐肅宗借口「兩日來疹病」,竟未謀面。當玄宗一行欲由夾城返南內時,突發變故,「忽聞戛戛聲,上(玄宗)驚回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禦馬,輔國便持禦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禦!’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即攏禦馬,直至西內安置。」[41]
局面之驚險緊張,確乎令人心驚。事後,「上皇泣曰:‘微將軍,阿瞞已為兵死鬼矣!’」[42]
諸書所載逼宮一事,均說是李輔國「矯詔」「矯敕」所為,與唐肅宗全無幹系。但是,從李輔國叱高麗仕「大不解事」以及唐肅宗事後對李輔國等人所說「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43]可知遷宮之事自有隱情。
所謂「防微杜漸」,就是擔心唐玄宗尋機龍飛,再掌朝綱。何況此時唐肅宗多病,而唐玄宗雖已七十六歲,依然宴飲聚樂,並未顯出老邁龍鐘之態,唐肅宗確實不能不有所防備!
因此,逼宮之舉是唐肅宗為進一步控制唐玄宗而部署的,李輔國自當秉承其旨意無疑。
唐玄宗入居西內,遂每日與高麗仕「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44]。不久,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被勒令致仕,高麗仕被削職除名,長流巫州。兩位親信遠離而去,「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刑部尚書大臣顏真卿首率百僚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45]。
這與唐玄宗在蜀之日,唐肅宗君臣奏表絡繹不絕的情形相比截然不同。此時的唐玄宗已完全成為唐肅宗控制下的孤家寡人。此後的唐玄宗,精神郁悶,再無生趣,從此開始辟谷。
風雲一生的唐玄宗在喪失政治權力後,百無聊賴,身體也迅速垮掉。寶應元年(762年)四月甲寅,七十八歲的太上皇郁郁而終。十三天後,唐肅宗駕崩。父子之間圍繞著權力而纏結不清的關系就此結束。

有筆記記載基哥被盜墓
腦袋是被劈成兩半的
由上述可知,自唐玄宗由巴蜀返京,肅宗朝中央政局的二元色彩遂開始淡化。上元元年(760年)將唐玄宗逼遷至西內,更為二元格局崩潰之征兆,太上皇唐玄宗與皇帝唐肅宗先後死去,使這一政治格局最終解體。
唐代宗即位後,先為高麗仕平反,並許其陪葬唐玄宗泰陵,「喪事行李,一切官給」[46];唐玄宗時期被廢黜之「故庶人皇後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宜並復封號」。就連永王璘也被平反昭雪。[47]這標誌著唐代宗擺脫了肅宗朝二元政治格局的陰影。
但是,唐肅宗在此政局下確立的施政方針、平叛方略等給唐代宗朝乃至整個唐後期政治帶來的影響,並沒有因二元格局的解體而消弭。
如對擁兵藩帥的姑縱、宦官勢力的崛起等,無不可從肅宗朝中樞政治中求其肇始之基。
註釋:
[1] 【舊唐書】卷111【高適傳】第3329頁:「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
[2] 關於【永王東巡歌】的箋解,歷來詩家頗有歧異;對其中的天子、帝、君王諸詞語,尤多聚訟。我覺得,詩中之帝、君王為玄宗而不是肅宗,賢王為永王,可信從。參見薛天緯【李白與唐肅宗】,載【學林漫錄】第9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86—98頁。
[3]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註】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546—555頁。
[4] 【舊唐書】卷107【永王璘傳】,第3264頁。
[5] 周紹良:【唐代墓誌組譯】,建中004,第1823頁。
[6] 【全唐文】卷350,李白【天長節度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第1569頁。
[7] 【唐大詔令集】卷36【停潁王等節度誥】,第140頁。
[8] 賈二強先生指出「此誥不無疑竇」,又說:「此誥真偽姑置不論,至少我認為是否代表玄宗本意大成問題。」見賈二強【唐永王璘起兵事發微】,【陜西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第86頁,註二。林偉洲先生也認為「誥命本身仍充滿著疑問」,並認定「此誥命為偽撰,而且應出自肅宗,作偽目的當然在否定前【命三王制】諸子分鎮之效用,惟撰作時間不可能太早」。見【靈武自立前肅宗史料辨偽】,載【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745—768頁。按:林文中雲「【唐大詔令集】題為【停永王等節度誥】」者,「永王」系「潁王」之誤。
[9] 【舊唐書】卷112【李峘傳附峴傳】,第3343頁。按:【通鑒】卷219「肅宗至德元載十一月」條第7007頁載其為江陵長史;【舊唐書·李峴傳】第3348頁未載其曾經任永王副使事。李峴歸肅宗而未從永王,宜乎【舊唐書】傳「贊」稱其「獨守正」也。
[10] 【舊唐書】卷107【永王璘傳】,第3264頁;【通鑒】卷219「肅宗至德元載十一月」條第7007頁略同。
[11] 【舊唐書】卷107【永王璘傳】,第3266頁。
[12] 【通鑒】卷219,肅宗至德二載二月,第7020頁。
[13] 【唐大詔令集】卷39,第162—163頁。
[14] 賈二強:【唐永王璘起兵事發微】,【陜西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
[15] 【通鑒】卷219,肅宗至德元載十一月,第7007頁。
[16] 【通鑒】卷219,肅宗至德二載二月以及胡三省註,第7018頁。
[17] 【通鑒】卷219,肅宗至德二載八月,第7031頁。
[18] 【通鑒】卷220,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第7044頁。
[19] 【讀通鑒論】卷23【肅宗】五,第794頁。
[20] 【通鑒】卷220,肅宗至德二載九月,第7035頁。
[21] 此事在【通鑒】卷220「肅宗至德二載九月」條中與【新唐書】卷139【李泌傳】中載之甚詳,可以參見。
[22] 以上請參見【通鑒】卷220,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十月,第7035、7041頁。
[23] 王吉林的【從安史之亂論肅宗一朝唐代政治與宰相制度變動的綜合研究】一文即從這一角度進行了考察,具體情況可以參看,本文不另贅述。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下冊,第783—804頁;又載氏著【唐代宰相與政治】,第208頁。
[24] 【舊唐書】卷10【肅宗紀】,第245頁;【舊唐書】卷112【李麟傳】第3339頁同。按:【新唐書·玄宗紀】【新唐書·宰相表中】作至德元載十一月,誤。參見王吉林前引文,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下冊,第791頁,註42;又見【唐代宰相與政治】,第235頁,註42。
[25] 【舊唐書】卷112【李麟傳】,第3339頁。又雲:「時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
[26] 據【全唐文】卷350,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第1570頁:韓仲卿,「尚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說明崔渙在成都為相與任使江淮均有行政權。
[27] 【舊唐書】卷108【韋見素傳】,第3278頁。
[28] 【舊唐書】卷111【房琯傳】,第3321—3322頁。
[29] 【舊唐書】卷108【韋見素傳】,第3278頁。
[30] 【舊唐書】卷111【房琯傳】,第3322頁。
[31] 【舊唐書】卷111【房琯傳】,第3322頁。
[32] 【通鑒】卷221,肅宗上元元年六月,第7093頁。【舊唐書】卷184【李輔國傳】第4760頁略同
[33] 【楊太真外傳】卷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144頁。【高麗仕外傳】,同上本,第119頁。【明皇雜錄】第46頁【補遺】載同。
[34] 【舊唐書】卷10【肅宗紀】,第254頁。
[35] 【楊太真外傳】卷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143頁。
[36] 【明皇雜錄】第66頁【輯佚】。【楊太真外傳】卷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143頁略同。
[37] 【舊唐書】卷184【李輔國傳】,第4760頁。
[38] 【通鑒】卷221「肅宗上元元年六月」條第7094頁胡三省註:「李輔國此言,是臨肅宗以兵也。」
[39] 【通鑒】卷221,肅宗上元元年六月,第7093頁。
[40] 【舊唐書】卷184【李輔國傳】,第4760頁。
[41] 【高麗仕外傳】,【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143頁、第119—120頁。
[42] 【次柳氏舊聞】「補遺」,【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9頁,據【類說】卷21補。
[43] 【通鑒】卷221,肅宗上元元年七月,第7095頁。
[44] 【高麗仕外傳】,【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120頁。
[45] 【通鑒】卷221,肅宗上元元年七月,第7095頁。
[46] 【高麗仕外傳】,【開元天寶遺事十種】本,第121頁。
[47] 【唐大詔令集】卷2【代宗即位赦】,第8頁。
本文節選自【唐代肅宗玄宗之際的中樞證據】,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先發。該書理清了安史之亂前後的若幹伏線,令讀者能夠更清晰的認識唐肅宗一朝的實質,感興趣的朋友推薦入手。
歡迎關註文史宴
長按二維碼關註
專業之中 最通俗 ,通俗之中 最專業
熟悉歷史 陌生化 ,陌生歷史 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