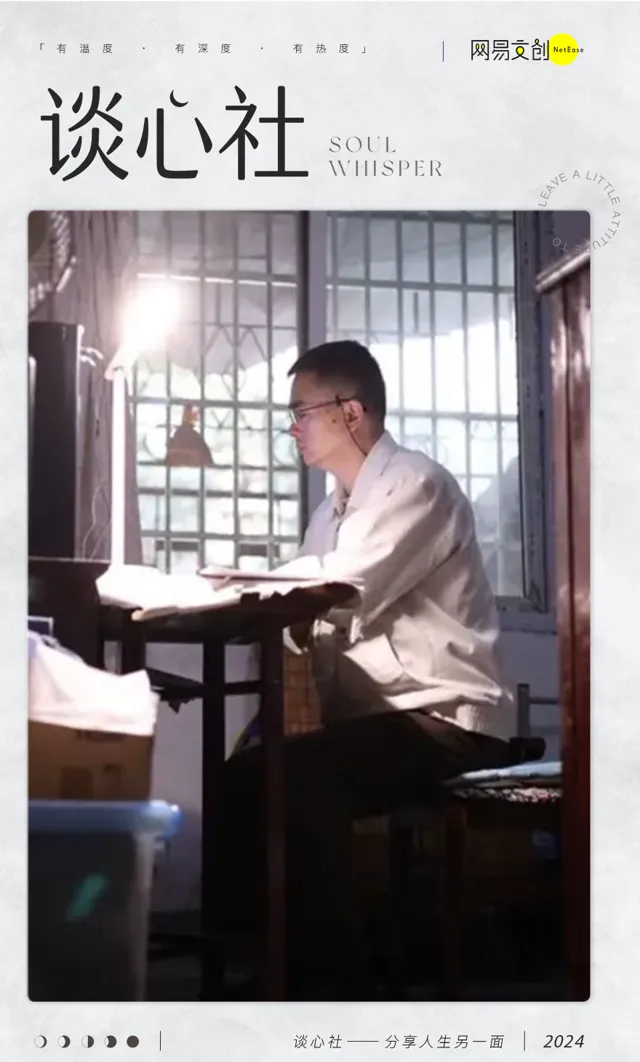
▣ 公號:極晝工作室(ID:media-fox)文 | 殷盛琳 編輯 | 王珊瑚
2022年初,【杭州日報】刊載了一位父親的長信,講述患有躁郁癥的「天才兒子」金曉宇,常年蟄居在家,卻自學英、日、德等語言,轉譯多本著作。文章刊發後,迅速引燃社群網路。
當時,父親金性勇說,他的願望是把兒子「推出去」,讓他被這個社會看見,將來有個依靠:
2022年末,我曾回訪這對父子,當時金性勇在努力吃鈣片、喝野人參水,想努力多活幾年,怕兒子一個人太孤單了。金曉宇也有意識地訓練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跟父親學習為人處事。
但之後不久,金性勇就生病住院,沒能走出那個冬天。金曉宇在52歲這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獨居生活,他在現實日常中懶散而失控廚房的地板遍布泥漬,抹布破掉也不知道在哪裏找新的替代,時常忘記東西放在哪裏。
但在另一種層面上,失去至親之後,他反而松弛自由,開始像普通的中年男人那樣活著。
1
漫長的托孤
我要捐獻我的遺體。我說她(妻子)走了以後,我沒有必要做墳墓。你(曉宇)自己單身一個人,對吧?哥哥十年、八年回來一趟,沒有人去上墳的。沒有意思的。
——金性勇,2022年12月29日
金曉宇始終記得父親金性勇最後的樣子。紫紅色的血瘀從左胸蔓延開來,腹部、背部,全是,像悶刻在皮膚上的銘印。父親的身體變得極瘦,薄薄一片,看起來只有骨架撐起那件深藍色做底的壽衣。
沒有葬禮,親戚們在醫院的太平間舉辦了簡單的告別儀式。他頭腦昏沈,站在人群中間,忘記了哭泣。幾個小時後,省紅十字會的人將父親的遺體拉走了,此前,金性勇簽署了遺體捐獻誌願書。三年後,才能領取骨灰。
對金曉宇來說,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了。父親去世前一周,醫生還說治療差不多結束,可以出院了,只是需要註意體內的血栓。但很快,父親的病情就急轉直下。最後送進重癥監護室之前,醫生告訴他,有95%的可能性是出不來的,「連九死一生(的機率)都達不到」。2023年1月18號下午,父親沒能捱過去。「我想回去總能回去的,沒想到回不去了」,金曉宇連恐懼也是後知後覺的。
事實上,這次住院前,金性勇的身體已經出現了征兆。他八十多歲,胃口變得很差,連軟糯的茄子也吃得少了,腳腫是頭幾年就有的毛病,腎臟的問題,走路變得越來越困難。金曉宇勸過幾次父親到醫院看看,金性勇都拒絕了。金曉宇說,父親害怕進醫院,「他怕進去就出不來了。」去世前一段時間,金性勇曾喝野人參泡水、吃鈣片,自己測量並記錄血壓數值,努力想要維持健康,多陪陪曉宇。
這次住院是實在無法繼續拖延。2023年1月初,杭州冬天陰冷入骨,金曉宇看到父親把客廳的電風扇開啟,獨自坐在沙發上吹冷風。父子倆無話。到了晚上,他被門外啪嗒、啪嗒的聲音吵醒,起來發現是父親在按廚房那盞燈的開關,「一會兒開,一會兒滅」。接著,父親開始用剪刀剪餐巾紙,塞進嘴貝瑞,神誌已經不大清楚了。曉宇趕緊給社群打電話,將父親送進醫院。
當晚,表哥張錚幫忙回去拿了鋪蓋行李,金曉宇開始了半個多月的陪護。之前許多年,都是父親接送他去精神病院,這是金曉宇第一次陪護父親。他每天的行程幾乎固定:晚上住在病房,三頓飯也在醫院吃,吃完中飯後,他回家一趟,在沙發上靠著休息一會兒,透透氣,然後再去醫院。
金曉宇說,父親在生命的尾梢,睡眠變得極少。到了晚上,金性勇就坐在病床邊,有時整夜無眠,不知道在想些什麽。除了提出上廁所之類的基本需求,他對曉宇沒什麽交代。
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位老人的心事是什麽。
2021年10月,金曉宇因躁郁癥再次住院,那時他的母親已經躺在病床上完全無法行動。金性勇在幫妻子餵飯、翻身的間隙,手寫了一封長信,寄往【杭州日報】的副刊,將自己的「天才兒子」,一個在過去十幾年來,轉譯英、日、德多語言的譯者金曉宇「推出去」。文章發表後,迅速在社群網路上引起熱議。金曉宇也成為了浙江省轉譯協會的一員,「有組織有團體」,有了依靠。

金曉宇說,自己當時根本想不到父親能撐起這麽大的場面。如果不是因為父親「鬧這麽一通」,他可能會面對完全不同的處境,「在精神病院待著,永遠在那裏待著。」他想象那樣的生活,像「孤魂野鬼」,吃很多藥,大便解不出,肝腎可能受損,轉譯更是幹不了。最重要的是,沒人會接他出去。
父親去世後,金曉宇開始斷斷續續地整理遺物。在客廳陳舊的書架上、抽屜裏,他翻出了厚厚一沓信紙,是金性勇當時寫給【杭州日報】那封信的底稿。金曉宇此前只知道是父親廣為流傳的那封信,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但他當時正在精神病院,並不清楚事情經過。「原來縫紉機放在陽台上面,他自己一個人拖去屋裏,當桌子(在上面)寫,修改好多遍。他不會用電腦,只能一遍遍用手寫。」他不知道父親是哪裏來的力氣拖動那台縫紉機的。
講不清是不是父親去世的悲痛難以消解,之後沒多久,曉宇就發了病,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杭州七院)。第一次是在面館推搡了去用餐的環衛工,在七院住了兩個月。第二次,曉宇獨自搭地鐵去了紹興,出站時,和當地路人發生沖突,社群和派出所的人一起開車把他接了回來。又送進了七院。
在精神病院,金曉宇每周都有一次通話的機會。他只記得兩個號碼,一個是家裏的電話,一個是父親的手機號。但這次入院後,他不知道該打給誰,接他電話的人已經不在了。
2
作家、抹布與面館
他(曉宇)兩三個星期掃一掃(地),今天三個房間掃好了,明天三個房間要擦一遍,而且地要擦兩遍,這些都是他做的。以前給他媽媽做,媽媽做不動了,(後來)我也做不動了。
——金性勇,2022年12月29日
兩次發病後,金曉宇的堂哥和社群一起,為他在杭州市殘疾人托管中心爭取了一個床位。這是金性勇還在世時就申請過的,原本他打算和曉宇一起住進去,但後面發現自己不符合條件。2023年夏天,父親去世半年後,金曉宇一個人搬了進去,在裏面待了110天。
他說,自己在那裏是數著日子過的,「度日如年」,再也不想進去了。
托管中心裏訊號很差,發微信都困難,金曉宇說。食堂裏吃得也不合口味,油放得很多,在裏面近4個月,金曉宇的肚子大了一圈,臉也有些浮腫。「在裏面基本不鍛煉,大家在那裏呆坐著,走路都不太走。」三餐是定點,早上五六點鐘就要起床,早午飯後有集體活動。他總是失眠,晚上睡不著,中午也睡不著。
金曉宇說,在裏面住著的人,主要分兩類,精神殘疾或者智力殘疾。宿舍是三人間,他住進去的時候,一個室友請假出去了,只剩下一個活潑的「表演家」。表演家每天三、四點鐘要起床,在廁所排練節目,「一種像舞蹈一樣的柔力球運動」。每天晚飯後,他喜歡領著大夥一起排練。
在托管中心,金曉宇最好的朋友是一位「作家」。作家的被托管經驗相當資深,已經在那裏待了6年,在進去之前,他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幾年。
作家和金曉宇差不多大,熱衷於寫作半紀實的虛構小說。他給曉宇看過一些,主要寫在托管中心的故事,與養護員之間的故事。他不看金曉宇轉譯的小說,只喜歡聽武打小說。金曉宇記得,作家一天到晚拿個MP4,聽1000多集的大部頭。
金曉宇在裏頭沒多久就後悔了,想要出去。他跟社群、堂哥原本約定的是,先體驗一、兩個月。但因為一些特殊狀況,直到2023年10月底,他才給表哥發微信,讓對方接自己出去,但表哥說不行,他要開會。金曉宇又給堂哥發微信,最後堂哥把他接了出來。
金曉宇覺得好在是虛驚一場,但他再也不想把自己陷入那樣的境地了,「沒人接的話,可能出不來的。」他從托管中心回家後,和社群黃書記約定,只要能維持住不發病,可以暫時不住托管中心。但黃書記說,目前他是以請假的名義出來的,托管中心仍然保留著他的床位。
金曉宇回到熟悉的房間,開始一個人生活。即便之前就有意識地學習如何獨自生活——母親離世前,他曾在筆記本上記錄下十道素菜、十道葷菜的做法,父親在世時,他在旁邊努力學習如何為人處事——但當至親真的離開之後,他才發現許多事情沒法透過練習而掌握。
比如廚房的抹布,他很快用破了,又不知道去哪裏找一塊新的來替代,就還用著舊抹布。衛生紙、洗潔精,都是以前囤積下來的,他也盡量保持著父親在世時,原有的生活秩序。
但很快,他發現這樣的狀態無法長久保持。做飯是首要難題,金曉宇說,之前父親在世時,兩個人分好工,自己只需要買菜、洗碗就好了,其他的父親來做,他沒覺得有多辛苦。現在,他需要買菜、洗菜、切菜、做飯,再洗碗,發現做家務的時間被無限拉長。他幾乎被消耗掉所有精力,沒有力氣再做轉譯。

後來,社群為他想了個辦法,每個月交給對面樓一戶鄰居2000塊錢夥食費,跟人「搭夥」。但一個月之後,鄰居不幹了。黃書記說,人家覺得曉宇要求太多,菜要吃煮得很爛的,燒起來麻煩得很。
吃飯搭子散夥後,金曉宇輾轉在周邊的幾家面館,是幸福裏面、蘭州拉面的常客。他說,周邊蘭州拉面開了三家,現在第四家也開張了,正在裝修,每家口味都不一樣。偶爾,他會到麥當勞或德克士改善夥食,吃頓「大餐」。他牢記速食店的打折日,並充值了優惠卡——他為自己設定的生活費上線也是2000元。
父親去世後,留給曉宇的遺產目前存在表哥那裏,怕他發病後受騙或隨意揮霍。 他並不拮據,之前一家網站要他授權拍攝電影,給了一筆不小的費用。金曉宇只保留了小部份生活費,他已經習慣節儉,也想為自己的晚年多攢點錢。獨居後,他最奢侈的一筆開支是花400塊買了一件打折羽絨衣。
他幾乎不拖地,覺得「一個人在家裏,打掃衛生沒什麽勁頭」。餐廳的地板上,泥漬變幹後牢固地附著在上面,金曉宇踩來踩去,兩個多月沒有處理過。空藥瓶落在了餐桌下面,他看到了,用腳踢向更深處。2024年2月底,杭州開始下起連綿的冬雨,空氣裏氤氳著冰冷的水汽。金曉宇在室內不斷自言自語:「冷死了」,但始終沒有開啟空調——一個人開空調顯得多余浪費。
金曉宇經常找不到東西放在哪裏。有次他要出門,找一個牛津包,遍尋房間也找不到,還有電熱毯,也失蹤不見。以前東西都是父親找,「他很會找東西」。
在一些很平常的瞬間,金曉宇會驚覺,原來母親、父親都不在了。去餐廳吃飯,他看到蔬菜炒雞蛋,說這道菜爸爸也會做。聊到衣服,他記得爸爸有件鱷魚牌的襯衫。在空蕩蕩的房間裏打轉,他指著餐桌說,最開始坐在那裏的是4個人,後來哥哥去了國外,變成3個,媽媽生病去世後,父子倆坐在那裏。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3
影子夢魘
父愛放在兩個人身上都是同等的,但是在曉宇身上我增加一份同情心,更多的關心,我不否認這點。
——金性勇,2022年12月29日
金曉宇一直惋惜,父親的生日是農歷四月初九,如果他還在,今年應該是88歲生日。以前父子倆每年過生日,都會到面館吃一碗「蝦爆鱔面」。再熱鬧一點的場景,都發生在久遠的過去,哥哥還在的時候,兄弟倆過生日,媽媽會買來蛋糕。
父親去世後,金曉宇對哥哥金曉天的情緒變得更復雜。當時,所有親戚都聯系不到這位已經移居澳洲多年的哥哥,發微信也沒有回音。表哥張錚說,他們最後是求助了派出所,透過公安系統找到了金曉天的聯系方式。
得知父親去世的訊息後,金曉天當即買了回國的機票。除了辦理財產公證等手續,這次回來,他要處理兩位至親的後事——2021年,母親曹美藻去世後,骨灰盒一直放在殯儀館,她的遺願是等曉天回來安葬。
金曉宇說,哥哥回國後,在親戚的陪同下去選了一片墓地,打算為母親舉辦葬禮,也將父親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算是合葬。
葬禮那天,他和哥哥一起去了殯儀館,領回媽媽的骨灰,再到墓園去。按照習俗,下葬時需要撐一把傘,不能讓陽光照到骨灰盒。從下車到墳墓那段路,要一直撐著。曉宇記得當天是晴天,他撐著傘,哥哥抱著媽媽的骨灰盒,一起走上山去。那是這麽多年來,兄弟兩個最親近的瞬間。很難講清當時的感受,金曉宇說,有些疏遠,陌生,但他知道,這是世界上自己唯一的至親了。
2023年冬至,金曉天又回來過一次,他的妻子、一對兒女也回來了,為父母掃墓。回國後,金曉天到老房子裏去過兩回,曉宇覺得他比以前客氣一些。哥哥從澳洲給他帶了一雙羊皮保暖鞋,還有蜂蜜、維生素一類的保健品。但曉宇說,哥哥只站在客廳,環顧四周看看,沒到裏面的房間去,維持著一種微妙的界限。
金曉宇思量很久,決定把爸爸遺物裏那塊手表給哥哥,留作紀念。曉宇說,那塊手表跟了父親很多年,是去廣州出差時帶回來的新鮮玩意兒,承載了這個家庭分崩離析前很多美好的回憶。
他說,這兩年自己因為轉譯,有了點成就,才覺得和哥哥「平等」了一些。之前的許多年,兄弟倆的命運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金曉天也成為了金曉宇難以驅逐的夢魘。
金曉宇已經記不清兄弟倆的關系具體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壞的。廣為流傳的故事裏,金曉宇不幸的開端是因為童年一場意外,被鄰居家小孩用氣槍打壞了眼睛,而哥哥正好坐在旁邊,也沒有及時告知父母。但金曉宇說,他從未因此記恨哥哥,他對哥哥的憤怒,也並不來源於此。
他記到現在的有兩件事。第一次是小學的時候,他在學校遭到老師批評,心情很糟糕。當時金曉宇壓力大時喜歡偷東西,就把同學的筆和本子偷回了家。在未鎖門的鄰居家,他還偷拿過5塊錢,以及人家的香煙殼。當時他和哥哥住一個房間,金曉宇把這些事寫進了日記本,放進寫字台的抽屜裏。鎖是壞的,哥哥還是看到了。後來,爸媽也知道了。
另外,有次中午,哥哥讓他藏起來,中飯也不要出來。金曉宇很聽話,躲到角落裏頭,餓得要命。爸媽問哥哥,曉宇怎麽還沒回來,他聽到哥哥說,不知道。
初中之後,哥哥就像一個如影隨形的完美參照物。金曉天數學很好,成績常年靠前,考上了復旦大學。而金曉宇那會兒已經開始休學,沈迷圍棋,處在躁郁癥的初期。哥哥考上名校的暑假,買了一個出門用的皮箱。金曉宇心理壓抑極了,把皮箱從當時住的四樓扔了下去。
從復旦畢業後,金曉天在杭州一家銀行工作,認識了當時的女朋友,沒多久就結了婚。知道哥哥要舉辦婚禮的時候,金曉宇大鬧一場,把家裏東西都砸了。「憑什麽他什麽都有,我什麽都沒有?」他缺席了哥哥的婚禮現場。
1998年,金曉天去澳洲讀MBA,最開始還會回家來看看,但每次回來,金曉宇的病情都會加重一次。後面,父親金性勇幹脆把金曉天往外推,叫他少回來一些。在回國處理父母後事之前,金曉天已經接近10年沒有回來。
在金曉天離家的20多年中,曉宇只收到過哥哥寄來的一封信。那時曉天出國沒多久,寄信來問候新年快樂。在信裏,他告訴曉宇自己正在做清潔工,為老板開垃圾車。曉宇說,後來哥哥在報社工作過,效益不好,倒閉了,如今在一家輔導機構做老師。
這次哥哥回來後的幾次親戚飯局上,兄弟倆沒有坐在一起。曉宇只能從哥哥和別人的閑聊中,偷聽到他零星幾件事情。在飯局上,哥哥不愛講話,喝點酒,才講一兩句,「他說全家到南京去玩去了,現在南京到處都要收門票。」
處理完父母後事後,在表哥張錚的見證下,兄弟兩個平分了父母留下的遺產。曉天把自己的那部份同樣交給了張錚保管,讓他用於曉宇的生活。
事實上,金曉宇在整理父親的遺物時,還發現了一封父親寫給哥哥的信。在信裏,金性勇詳細記錄了曹美藻生前最後的狀況,並告訴曉天,自己一直很想他。
但出於一種說不清的情緒,曉宇最終也沒有把信交給哥哥,「給他也不會有什麽反應的」,他說。

金曉宇在附近的餐館吃「蝦爆鱔面」,之前每次生日時,他都要和父親一起吃面。殷盛琳 攝
4
另一種自由
兩年前,金曉宇轉譯時,需要將電腦文件顯示比例放大到155%,如今需要到200%。他52歲,已經進入中年深處,無論是年少時就摘除晶體的右眼還是左眼,都已經很難長時間註視螢幕。這兩年,他覺得自己體力也下降了許多,有了衰老的痕跡。
之前的許多年,他受躁郁癥所困,被父母養在家裏。在人生的關鍵選擇上,幾乎都是由母親在幫他做決定:轉學、參加成人自考、讀最流行的國際貿易專業、學習語言做轉譯。母親相信一個道理,「小車不倒只管推」, 金曉宇曾說,自己在家裏選擇服從。
獨居的孤獨是真實的,但在所有至親離開,推著「小車」的手悉數松開後,金曉宇反而變得更松弛。他孑然一身,不再是誰的天才兒子,也不必時時扮演一個認真的轉譯家。某種意義上,他「自由」了。
以前,他在外面總是睡不著的,但上次跟著杭州譯協的人到富陽開會,他意外地睡得很沈,會議主題是給公共場合的中英文轉譯糾錯。
金曉宇開始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不再嚴格遵循一個計劃表。像個普通的中年男人那樣活著。晚上,他經常拿手機在百度上看短視訊,搞笑類的,或者民間獵奇。他看象棋小神童的對局,也知道西安有活人渾身塗滿顏料,在熱鬧的景點扮演「銅人」。有時候能刷到淩晨一兩點。他把視訊開外放,音量很大,在空空蕩蕩的房間裏回響。

金曉宇坐在臥室的老舊桌子前做轉譯。殷盛琳 攝
他看起來生活不怎麽規律健康,時常犯懶,但神奇的是,在過去的這個冬天,他與疾病相安無事,沒再入院過。「現在沒人跟我吵了,不太會犯病了。」金曉宇說,之前自己總是被管束,開始是母親,母親去世後,這個角色由父親替代,最好什麽事都聽他們的,如果不聽,就要發火。他也會跟著吵起來,摔東西控制不住,就上醫院去了。
社群黃書記記得有一回,她勸曉宇吃飯換換口味,不要總吃一種,曉宇說,你這樣的話就跟我媽媽一樣,「我後來想想,也可能以前爸爸媽媽也是管他這麽多的。」但獨自生活後,黃書記覺得曉宇長大了一些。上次同學來看望他時,帶來了國外的巧克力,他拿到社群辦公室,分給了大家。「他還是有自己的主意的」。
除了日常吃飯,金曉宇如今幾乎不怎麽出門。父親去世後,他最多是到運河邊走走,最遠距離是走到枯樹灣巷,從地圖上看,離家不到1公裏。他在現實裏為自己圈定了安全範圍:以家為軸心,一公裏為半徑。超過這個距離,他會感到不安。「出去以後犯病的話,家裏沒有人了,死在哪裏都不知道。」
2024農歷新年過後,金曉宇的中學同學組織聚餐,微信群裏很熱鬧。曉宇記得有人調侃,等大家的股票回升到「3000點」再說AA的事,這次先由在美國發展的同學請客。他不太清楚其中含義,覺得老是讓別人請客沒什麽意思,幹脆拒絕了。之前,金曉宇參與過一次同學會,已經進入中年的大家圍坐在一起,談論的話題無外乎家庭、事業與時下新聞,他都興趣寥寥。
之前,父親金性勇想幫他找個物件,有個照看。金曉宇曾和一位江西的女士接觸過一陣子,但無疾而終。
如今,他能把握的只有轉譯。金曉宇仍在轉譯本雅明的【拱廊計劃】,一共1200頁,是本雅明從1926年到1940年自殺前,有關文化、歷史、哲學、建築、經濟等方面所搜集的材料和筆記。以前,金曉宇會想著每天多翻一些,但現在,轉譯成為他度過生命的一種方式,他反而希望慢一些。「我什麽也不想,每天能轉譯一點是一點,就是在拿轉譯耗時間。」
轉譯是他接下來人生中唯一的計劃。他說,先爭取到60歲,完成60本書的轉譯,之後每年轉譯一本,直到死亡來臨。
本文轉載自【極晝工作室】
關註檢視更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