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英語教師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今年31歲。她和家人住在巴勒史坦加薩走廊最南部、靠近埃及邊境的城市拉法(Rafah)。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越境突襲以色列、殺害1200余名以色列及外國公民後,以色列旋即對加薩走廊展開報復性軍事打擊。據加薩衛生部數據,截至2024年6月12日,加薩已有超過37202人被殺害,另有84932人受傷。
以軍沿加薩走廊自北向南進行地面行動,加薩人也自北向南不斷逃亡,最多時有140多萬人聚集在拉法避難, 拉法因此被稱為「加薩最後的避難所」。
戰爭爆發後,阿伊莎的工作難以為繼,生活陡然改變。她開始為難民營流離失所兒童做心理援助,以此作為戰時生活的精神支柱。
過去8個月以來,我們一直和阿伊莎保持著聯系。 她常常在通訊軟體裏發來斷斷續續的語音資訊,描述她的日常,關鍵詞通常是轟炸、缺水、恐懼與熟人的死亡,但也偶爾有笑聲、友誼與希望。
2024年4月中旬起,以軍稱要對盤踞在拉法的哈馬斯24個營中最後6個營進行清剿,因此將在拉法展開地面軍事行動, 百萬民眾開始從「最後的避難所」撤離。阿伊莎和家人也不得不離開家園。此後,她幾度消失在通訊訊號的黑洞裏。
我們根據對阿伊莎的語音采訪和通訊整理了這篇口述,描述她所見證和親歷的戰爭。
口述 | 阿伊莎·沙克法
采訪整理 | 程靖
編輯 | 徐菁菁
阿伊莎
從拉法撤離之前,我往行李箱裏裝了幾條裙子。一條是我一歲半時穿的小裙子,我想以後有孩子了,留給我的女兒穿;另一條是我媽媽結婚時穿的裙子,超級美,還有一條純手工制作的巴勒史坦傳統紋樣長袍,是我媽媽為我人生的「大日子」準備的。
我還拿上了五本書、從加薩海灘上收集的貝殼、我的學生和朋友們給我寫的卡片——簡而言之, 我「生活中的所有玫瑰」。 未來如果離開加薩,我想把它們都帶走。我的行李裏,既有我的過去,也有我的未來。
我們一家人要撤到汗·尤尼斯(Khan Younis)市,那是拉法以北的一座城市。那裏的網路幾乎已經被摧毀了,我很可能失聯。所以走之前,我一直在給親友們發資訊,告訴他們我去了汗·尤尼斯,如果我沒有訊息,也不要太擔心我。
現在,汗·尤尼斯是以色列軍方劃定的「安全區」,但鑒於他們在拉法劃定的安全區也發動過襲擊、也死過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活下來。 如果我不幸死了,你們悼念我的時候,記得要用我選的這一張照片 。

我叫阿伊莎·沙克法,是一名巴勒史坦難民女孩,今年31歲。 從小我爸爸就告訴我,要牢記我的「難民」身份。
我的祖輩來自加薩以北拉姆勒(Ramle)附近的一個村莊 (編者註:拉姆勒如今在以色列境內,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 。小時候,爺爺經常說起1948年「大浩劫」期間,他和家人逃難的情景:那天我的曾祖母正在廚房裏做飯,留下火堆和鍋裏的飯菜就走了,此後他們一生再也沒有回去過 (編者註: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國,埃及、約旦等國於次日向以色列開戰。這場戰爭連同1947年起因反對聯合國分治決議而爆發的巴勒史坦內戰,共導致約75萬巴勒史坦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期間約400個巴勒史坦城鎮和村莊人口銳減或被摧毀。巴勒史坦將以色列「獨立日」的次日5月15日作為「浩劫日」,即「Nakba Day」) 。
我的父母都是「大浩劫」後出生的。爸爸今年71歲,他在難民營裏長大,早年在加薩的聯合國近東巴勒史坦救濟和工程處(UNRWA)建立的學校當數學老師。上世紀80年代,以色列允許加薩人出國務工,爸爸就去沙烏地阿拉伯教書,把掙的錢寄給他的兄弟們,讓他們能夠有錢搬出難民營、在好一點的地方結婚成家。
我出生後不久,我們全家從沙烏地搬回了加薩。1997年爸爸在加薩經濟部謀了一個職位,直到2011年退休。爸爸把掙的錢都投入到了房子和孩子的教育上。他給我們修建的家距離海濱只有兩公裏,房子很寬敞、設施很齊全。他還把我們8個孩子都送進了大學。我們兄弟姐妹中有審計師、工程師。雖然我媽媽結婚前是一位化妝師,婚後就開始照顧家庭了,但我們家新一輩的女性中除了一個姐姐也是家庭主婦以外,都在工作。我有一個姐姐是計畫經理,另一個姐姐是教殘障學生的老師。

和我的祖輩、父母一樣,加薩是我離不開的故土。本科英語教育專業畢業後,我拿到了土耳其政府的獎學金,在土耳其伊茲密爾(Izmil)的一所大學讀了沖突和解碩士計畫。 留學的那段時間是我人生中最的快樂時光。在伊茲密爾,我第一次看見雪,我靜靜地站在視窗看呆了,連那天的土耳其語課都沒去上。
畢業以後,我確實考慮過留在土耳其。我適應那裏的生活,我也希望能自由地飛去不同的國家旅行,可是加薩連機場都沒有 (編者註:巴勒史坦領土唯一的機場位於拉法,1998年投入使用,2000年10月被以軍關閉) 。那 時,爸爸和我說,「你可以回來,也可以不回來,我給你選擇的自由。」 但我明白他話裏有話。我有一把爺爺老家房子的鑰匙,家人在我出國留學前把它做成了項鏈送給我,讓我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和祖國。
回到加薩後,我做過不同的工作:我為一家人力資源公司做英語演講培訓,同時進行著一項針對加薩走廊私營企業氣候適應問題的調研。我想做更多的事。2023年9月25日,我參加了聯合國近東巴勒史坦救濟和工程處英語轉譯職位考試。那次考試裏,50個人競爭1個崗位,但我經驗很豐富,考得很好。
我一心期待面試通知,可2023年10月7日,我的人生被打斷了 :那天清晨,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 (編者註:「阿克薩洪水行動」是哈馬斯對10月7日襲擊的稱呼) 後不久,整個加薩的學生、老師、職員,都被告知回到家裏呆著。 接著,以色列空襲了加薩走廊北部和中部的加薩城(Gaza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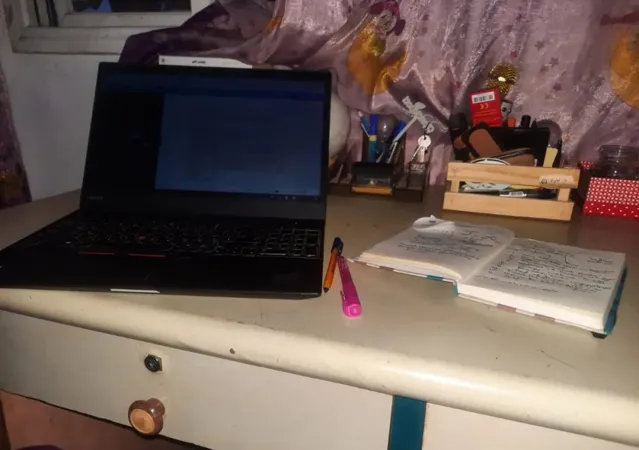
阿伊莎在拉法的家裏寫文書 (受訪者提供)
在戰時
說實話,自2008年12月以來,我和我的家人經歷了6次戰爭,轟炸的聲音我們已經很習慣了,如果離得遠一點我們也能睡得著。 你知道嗎,密集的轟炸發生時,加薩的孩子們不會嚇得顫抖,也不會躲進媽媽的懷抱,而是要跑去視窗看, 「是清真寺被炸了嗎?還是哪裏?」他們一點都不驚訝。
但這場戰爭和過去都不一樣。
10月9日,加薩知名記者、哈姆薩新聞(Al-Khamsa News)的主編薩伊德·塔維爾(Said Al-Taweel)就遇難了。我和他關系很好。他的離去對我來說是悲傷的開始。
10月22日,我發小的家被轟炸了。從我家客廳的視窗就能看到那兒。轟炸發生在那天傍晚,天黑之前。那時,她和丈夫、孩子都在醫院,逃過一劫。但她媽媽和妹妹都死了,丈夫的父親也死了。 她妹妹才17歲,剛剛透過了巴勒史坦高考,以後想做一個醫生。至於她母親,那是一位美麗善良的女士,我叫她「阿姨」,小時候總吃她親手做的飯菜。
兩天以後,10月24日,我堂姐和她一家人遇難了,在他們認為安全的避難所。我都不敢把這個訊息告訴媽媽。
12月6日,我聽說加薩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和知識分子裏法特·阿拉里耳(Dr. Refaat Al-areer)也死了。

裏法特·阿拉雷爾(右一)(來源於網路)
我第一次見到裏法特的時候17歲,是在拉法的一個英語培訓班上。他突然出現在教室裏,我們很驚訝,都瞪大眼睛看著他。他說:「女孩們,我們會相處得很好的。」我們都笑了。他很幽默,也很和善,但非常嚴格,8點,他會準點出現在教室,絕不允許遲到。
裏法特是加薩伊斯蘭大學的英語文學教授。在他出現前,我只是在學習英語這門課而已。 但他對英語的理念改變了我。
裏法特說,外界普遍認為巴勒史坦人「生活裏只有沖突」、「住在難民營裏靠援助過活」、「傾向於使用暴力」,而且「不了解世界」。 但我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有許多人性的共通點:我們都會開心、都會悲傷、也都會憤怒;不是所有人都愛好暴力,很多受過教育的巴勒史坦人愛好和平,希望全人類都實作和平。而一個英語說得很好的人能夠向世界傳遞巴勒史坦人正確的形象。比如說,英語讓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也讓我認識了你。
總之,上過裏法特的課之後,一個「新的阿伊莎」誕生了。
可是現在他死了。他生前在加薩城的一所聯合國學校避難,收到了以軍透過網路和電話發來的死亡威脅。此後,他離開了學校,回到了他姐姐家,在那裏遭遇了轟炸。同時死去的還有他的哥哥、姐姐和他們的四個孩子。
我必須慶幸,迄今為止我還沒有失去最親密的親人。我家裏原本只住了四個人:爸爸、媽媽、弟弟和我。10月9日那天,我的一個姐姐和她丈夫最先逃難住進我們家。又過了三天,另一個住在工業區伊比納(Ybina)的姐姐一家人也來了。他們家已經被轟炸摧毀,她兒子也受了傷,好在傷勢不太重。到拉法的時候,一家人從頭到腳蒙著黑色的灰塵,就在來的路上,他們剛剛目睹鄰居一家被爆炸撕成碎片。
10月中旬,加薩的天氣開始轉涼。我侄子想讓他爸媽回家取些厚衣服,但誰敢回去呢?親愛的,你真的沒法預料下一次爆炸會是哪裏。位於北加薩的賈巴利亞難民營(Jabalia Refugee Camp)的市場就是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轟炸的,50多個人被殺死了。以色列軍方還用了一種新的策略,叫做「火帶」:他們會同時轟炸同一街區的幾所房屋,加薩城的裏瑪爾(Al Rimal)街區就是這樣被徹底摧毀的。 現在每次洗澡之前,我要祈禱無數次才敢開始:我不希望在死去的時候渾身赤裸地被人看到的,好歹讓我把澡洗完,把衣服穿上吧!
「老好人」
從拉法撤離前,我家已經住了31個家人。最大的一間屋子睡了7個人。事實上,還有更多的人願意付高額的房租,想要搬進來。 爸爸都拒絕了:「我也想做好事,但如果我們家因為別人的原因被轟炸了,我該找誰負責?」
過去8個多月裏,我的生活基本是這樣的:每天清晨4點,我會起床做第一次祈禱。然後我需要睡個回籠覺。持續的戰爭下,市政早已完全停擺。拉法路上垃圾堆得到處都是,肆無忌憚的蚊蟲和轟炸聲一起,讓我沒有一夜能睡安穩。

阿伊莎現在住的家附近 (受訪者提供)
起床後,我會洗碗,做早餐。以前我們能領到一定量的援助物資,有面粉、食用油和糖。而且加薩的市場裏什麽都有,不同種類的起司、新鮮的水果蔬菜一應俱全。我有收入,我們能吃得很好。
現在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許多援助物資被倒賣,領到的援助變少,蔬菜水果的價格更是漲瘋了。 最誇張的時候,橙子1.5美元一個(1美元約合人民幣7.25元),西瓜20美元一個,一罐250克咖啡粉一度漲到33美元。媽媽喜歡吃香蕉,3美元一根,我只給她買,自己再也沒吃過,畢竟,不吃香蕉也不會死。草莓、獼猴桃、巧克力、蛋糕……這些東西我想也不敢想。
我們每天的主食是姐姐做的面餅。她和完面,把面團送到街角烤餅的大姐那裏去,家裏沒燃料,烤不了。我們吃餅子只能配罐頭,偶爾能吃到馬鈴薯、黃瓜和番茄。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把很多積蓄都花在了吃飯上,誰也沒有料到戰爭會持續這麽久。
在家裏,我總能聽見我姐姐吼她的孩子:「別換這麽多衣服,洗不了!」水電供應早已被切斷。 每天早晨,家裏的男性晚輩要去街上排隊取生活用水。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我們家31口人一共用27個水桶,容量從20升到40升不等,灌滿這些水桶要花6美元。取水的隊伍總是很長,人們總是因為排隊問題起沖突。我們還有一個1立方米的水箱,每周兩次會有人送水來,每次要付30美元。
好好洗一次澡已經成了奢望。 現在天熱起來,我一周最多能洗兩次澡。我很幸運,戰前我正好剪了短發。 為了不長虱子,我每次去拉法市區,還會找地方把頭發再剪短一些。城裏的理發店不再開張,但你能在難民帳篷裏找到流離失所的理發師。
市政供電在戰爭開始後第四天(10月11日)就中斷了。為了保持通訊,前幾個月裏,我只能到處找地方花錢給手機充電。今年2月,我哥哥和我各拿出了一大筆積蓄,湊錢買了一塊太陽能電池板。我們終於可以在家裏給手機充電了! 5月初,我們又用戰前10倍的價格買了4塊電池,把電池板和電池搭配起來,「發明」了一個發電機。我們還用不了電扇和冰箱,但至少可以開燈了!整整7個月來,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黑暗裏思考,我的眼睛甚至已經不再適應燈光。

水電食品的缺失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媽媽該怎麽辦。媽媽有糖尿病、高血壓,也有心臟病,她中風過三次,生活難以自理。她的藥是在拉法的聯合國醫院拿的。撤出拉法後,拿藥變得很困難。戰爭期間她精神壓力很大,兩次因糖尿病而昏迷,其中一次血糖過低,感覺她快要死了。
「我想回到孩子們身邊」
轟炸開始後,我的一切工作都暫停了,面試也遙遙無期。
但去年11月起, 我有了新的任務:我加入了一個援助組織,去拉法的各個避難所幫助流離失所的兒童。
今年5月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行動開始前,拉法都是「安全區」。 沒有地面軍事行動意味著沒有士兵和你面對面。滿載了逃亡人們的麵包車源源不斷進入拉法,有些人住在聯合國學校改成的避難所,其他人住在街邊的帳篷裏。海灣國家捐來的帳篷品質還不錯,但許多「帳篷」事實上就是一塊布、用幾根桿子撐在街邊,冬天下雨的時候,水會從四面八方滲進去。
每天,我都會路過數不清的帳篷,目之所及都是垃圾、垃圾、垃圾。住帳篷的孩子臉上很臟,頭發也很臟。婦女拎著水桶在街邊洗衣服,生起篝火做飯,用桶給孩子上廁所。我沒見過哪一個帳篷有足夠的睡墊。我見過一個家庭有8個人,每個人輪流睡那唯一的一張床墊,其他人就躺地上。
流離失所者的帳篷 (受訪者提供)
我們每周到避難所工作五天。這些地方和我家的步行距離都在10到30分鐘之間。走在路上,有時我能聽到有炸彈落在不遠處的一個地方。 每一次我都害怕極了,但只能調整一下呼吸,硬著頭皮繼續走。只要到了聯合國學校裏,我懸著的心就能落下了,我想,這裏比街上、甚至比我自己家裏都安全一些。
但聯合國學校有另一種危險,那就是極度糟糕的衛生條件。每座學校裏都擠進了上萬的男女老少,大家共用5、6個廁所,沒有水可以沖洗。 每個去過的同事都告誡我,「廁所裏面太惡心了」。在學校裏避難的婦女會和我哭訴,「我們實在忍受不了這裏的廁所了。」我只能安慰說:「這只是暫時的。」我想給她們一些希望。但事實上,我甚至沒有勇氣進那些廁所。我也害怕得傳染病,每次去學校都會戴上口罩。

在避難所裏,我們會帶孩子們做遊戲,這是他們難得能做回孩子的時刻。 我們的遊戲包括「放電影」「降落傘」。「降落傘」的意思是讓孩子們圍成一圈,抖動一塊狀似降落傘的尼龍布,也可以變換出多種玩法。此外,我們還會唱歌、跳dabke(一種阿拉伯舞蹈)。
我很擅長和孩子打交道。別的同事處理不了的調皮孩子,我都能相處得來。我最喜歡的孩子是馬利克(Malik),他有多動癥,實在太調皮了,連他媽媽都受不了他。但他其實很聰明,他的能量被誤解了。 我仔細聽他說話,就知道他什麽都懂。他也很愛我,每次我離開學校時他都會緊緊地擁抱我:「你明天一定要來啊!」
在去過半年裏,我想盡了一切辦法讓這份工作繼續下去。最難的是籌錢。我最早加入的援助組織從我們街區撤了出去,於是我和同事組織了自己的團隊。 我寫了一份計畫策劃,見了好多援助組織,人人都稱贊我做的事,但沒有一個人給我錢。
就在我走投無路,決定把我的金耳環拿去賣掉的時候,我在加薩最好的朋友聽我說了這件事,拿出了她存了很久的400美元積蓄借給我。後來,一位在法國的朋友也借給我1040歐元,我們把錢轉到加薩,光手續費就扣了100歐元。再後來我又拿到了一個科威特朋友的2000美元的資助。 我用這些錢購買了遊戲的材料,也給團隊成員發一些補助,這樣他們可以給家裏人買點物資,把生活繼續下去。

阿伊莎(左起第五)和同事在聯合國學校和孩子們做遊戲( 受訪者提供)
在我們的團隊裏,有人負責和孩子們做遊戲,有人負責拍攝工作照和視訊,還有一個女孩很會寫作,記錄人們的故事。 我知道很多人倡議說,要記錄戰爭中死者的故事,因為他們不僅僅是國際新聞裏的一個個數位,但我想,艱難時日裏活著的人的故事,也同樣值得被世界看到。
新家
5月19日,我在汗·尤尼斯街邊的「網咖」裏給你發訊息。這裏能付錢充電,充一次手機1個謝克爾(約人民幣1.93元)。這裏能上網,但網路不好。我給你發的訊息有些發出去了,有些沒發出去。 而且這裏距離我現在住的地方有3公裏遠,路上全是廢墟,走過來要1小時。
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因為之前的轟炸,窗戶沒了,只能弄幾塊布做遮擋。還有一個帶陽台的房間,墻壁沒了。我姐姐住那塊兒,幹脆沒有掛布。 她說,現在家裏住著好多非直系男性親屬,她在家裏也要穿戴整齊,和在街上沒有區別,幹脆敞著通風。萬一掛上了布,有人忘了這裏沒有墻,很容易跌下樓去。

我總是對自己說,也許有一天我會醒來會發現這只是一個夢。有時候我早上醒來,看到家人都在身邊,會不由地細細揣摩「活著」的感覺。 爸爸和弟弟還留在拉法的家裏,我每天早晨都想給他們打電話,確認他們是不是還活著。拉法在被轟炸,我們在這裏都能聽到聲音。等我回去的時候,我可能就沒有家了……
但現在我越來越不害怕了,如果輪到我們了,那就這樣吧。6月初,我收到了壞訊息,我之前提到過的那位的鄰居發小、「阿姨」的女兒和她的孩子也遇難了。 我相信她們一定是去了更好的地方。
我聽過一首歌,叫「親愛的朋友,來杜拜!」(Habibi,come to Dubai)。杜拜是個美麗的城市,我看過紀錄片,那裏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因為杜拜的旅遊業很發達,這首歌名變成了一個梗。
我想換個說法:「親愛的朋友,來加薩吧!」和杜拜不同,加薩不是旅遊目的地,而是一個「冒險」的地方,這裏有非常對立的東西——有生命也有死亡。我希望你可以吃到我媽媽和姐姐做的美味餅乾。如果你來的話,我願意把我的房間讓給你住。如果你夠勇敢的話,可以考慮來嗎?也許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我會無比開心地在這裏迎接你。

阿伊莎與廢墟合影,樓板上的字為「當一無所有只剩希望,那希望也帶著痛苦」 (受訪者提供)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排版:桃桃 / 稽核:米花
招聘|實習生、撰稿人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
本文為原創內容,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未經授權,嚴禁復制、轉載、篡改或再釋出。
大家都在看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