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從復旦大學博士畢業後,黃修誌選擇回到老家山東,在位於煙台的魯東大學任教。這是一所前身為師範學校的二本院校,有它自己的特性。另一位「出圈」的二本院校老師黃燈,常常為學生不確定的出路擔憂,而黃修誌發現,魯東大學的學生是過於明確自己的出路,將「考公、考研、考編」視為為數不多的選擇。他時常想,如果二本學生面臨的束縛是一個客觀事實,那麽身在其中的教師和學生可以主動做點什麽?
2018年,黃修誌主動向院領導申請,成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師範)專業1801班的班主任。在剛開學後不久的班會上,黃修誌提出幾項計劃:與每位同學聊天,舉行講座,建立班級微信公眾號,並由全體同學輪流撰寫班級日誌……再到後來,由1801班42位同學撰寫的班級日誌被匯集起來,成為【班史: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2018-2022)】一書。
黃修誌做這些事的初衷可以歸結為三個字:「不忍心」。黃修誌本科也畢業於一所二本學校,他屢屢在這些學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由此產生心有戚戚的共情。 對於黃修誌來說,每一次和學生的交談,都是平行宇宙中的兩個年輕人的對話。他們都在河流之中,只不過一個暫時在前,一個暫時在後。
實習記者|段弄玉
編輯|肖楚舟
口述|黃修誌
復制讀書歲月
說起我為什麽會辦【石榴花】雜誌、會組織同學們寫【班史】,可能還得回到我在山東東平三中讀高中的日子。我生長於東平的農村,後來我想,如果我當時去了全縣最好的高中,被分了快慢班,反而可能很難獲得這種自由閱讀和寫作的環境。
我們的校長是一個很有激情的語文老師,總是鼓勵大家廣泛地課外閱讀,辦各種課外活動。我到語文老師那去,老師就會從抽屜裏邊拿出幾本課外書,裏面有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文集,也有【塵埃落定】。我們班有70個同學,但我去閱覽室領報刊時老師總會給我80本,說剩下的10本報刊你自己看就行。老師們可能覺得這個孩子有想法,而且願意去讀去寫,所以就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種資源幫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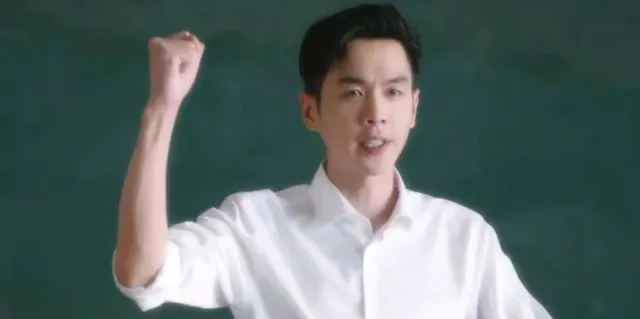
在聊城大學讀本科時,雖然圖書館裏的藏書更多,但我始終沒能再像高中那樣痛快地讀書。上大學後,我很快發現自己對課堂沒什麽興趣。和很多大學一樣,我們的老師基本上都是上完課就走。有一次我想請一位老師推薦一些書,他說稍後給我,就再沒有了音訊。即將要離開聊城大學的時候,一個關系特別好的舍友單獨請我吃飯送行。他跟我說,修誌,你需要一個好老師引導你讀書,這樣你可能會走得更遠一些。
後來到武漢大學讀研究生,我遇到了一些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其中有一位老師叫於亭,他雖然不是我的導師,但他每次跟自己的研究生的時候都會把我叫上。那時他講的最多的一點就是讀書不要求新,而要讀常見的經典,只有下盤足夠穩,根基足夠正,學問才能做得好。到了復旦,讀書的感覺更自由了,復旦有一句非官方的校訓,叫「做自由而無用的靈魂」。那時我們的課程沒有太多知識的講授,很多時候是老師和同學坐在一起讀一部經典,你一言我一語地講。甚至會有兩個老師同時坐在一塊講。那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騎著自由車,從圖書館到光華樓,再從光華樓到宿舍。每天晚上洗漱完了,就倚著床頭讀書,經常讀著讀著就睡著了。

我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如果你在一段歲月中喜歡上了一種氛圍並在後來無比地懷念它,你就會把這種氛圍復制到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當中。 所以剛來到魯東大學文學院的時候,我非常雄心勃勃,想著怎麽把復旦這種讀書的氛圍也帶過來。
但我發現很困難,我接觸到的孩子們大多不喜歡閱讀,有些自認為愛閱讀,其實只是愛讀小說而已。我就開始思考,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平台,讓這些愛讀書的同學能夠聚到一塊,抱團取暖?
所以我就主動向院領導申請,成為了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師範)專業1801班的班主任。我首先想到的是為他們辦兩場講座。我們學校大一新生入校後都要上晚自習,有一天我直接走進他們的自習教室做了一次關於「大語文」的演講,其實就是用粉筆在黑板上和大家邊講邊聊。因為我們1801班和1802班共用一個大教室自習,我也不好把另外一個班的同學趕走,所以就給兩個班的同學一起做了這場講座。後來1803班的班主任袁向彤老師問我,聽說你給一班和二班做了講座,為什麽不拉著我們三班?她聽說我們班還會有第二次講座,就組織了全年級的同學過來聽。這兩場講座後來就成為了石榴花大講堂的第一講和第二講。
做第一次講座的時候,班上的同學和我還不太熟悉。比如我記得當時想給一位叫路棣的同學安排一些班級工作,聊到一半,她突然告訴我說,老師,我們寢室要熄燈了,明天再說吧。那時還不到晚上十點,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還是有些詫異的。但這兩場講座之後,我們班的學生明顯對我親近了許多,很多同學發微信給我分享自己的感受,路棣也主動地來找我聊天。她講到自己總感到很難擺脫高考作文的寫作模式,想要自由地寫作卻找不到方法。當時我想我也不是作家,也解決不了這方面的困惑,但我們文學院有一位叫做周燊的老師,是一位作家,也是王安憶老師的學生,是不是可以約她給我們做一次講座。從周燊老師的講座開始,石榴花大講堂才逐漸地拉開了帷幕。

組織大家寫【班史】的過程也很類似。也是在一次班會前,我突然想到可以成立一個班級公眾號。當時我還沒有要出書的想法,只是想到有了公眾號,總得有內容貼上去,這個時候「班誌」兩個字就出現在了我的腦海之中。我學歷史出身,覺得地方有省誌、縣誌、村誌,那是否可以按照這種邏輯寫一寫「班誌」。透過寫「班誌」,我首先想促成大家一起做一件事,加強班級的凝聚力,同時也想幫助大家在對彼此的觀察中進行一種對自我的審視。在向同學們分享這個計劃時,我在黑板上第一次寫下了「班史」兩個字。我告訴大家,「班」是班固的班,「史」是太史公的史。他們確立了中國的史書的格局,後面的人都是沿著他們的路繼續往前走的。如果我們寫好了,後來的人要辦事時,就可以有所參考。
在考公大省,二本學生的困惑是什麽?
我很喜歡和學生聊天。在和大家的溝通中,我發現來到這裏的孩子們分兩種心態。對於一些同學來說,能考上魯東大學這樣的地方院校已經很滿足了。 可能因為沒有一本學校的資源和平台,不用去爭出國交流的機會或是保研的名額,大家有一種「窮開心」的感覺。 其中有相當一部份同學心裏是沒有主意的,因為父母期待他們去「考研,考公、考編」,社會上也覺得這些是更為體面的選擇,正好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麽,所以就加入這個大的群體了。 因為目標明確,做起來也只需要砸時間刷題,他們反倒沒有很焦慮。
另一種情況是,當大家接觸到更多的資訊,知道自己在全國高校的盤子裏是怎樣的處境時,就不免會產生一種落差感和心理波動。這種落差感在每年夏天的招聘會時尤其會加劇。在這些方面,他們可能更需要老師的引導。 這種引導倒不是說要怎樣提高學習效率,而是幫助他們破除應試教育的傷害和「二本院校」的標簽,讓他們能夠意識到,無論是一本學生還是二本學生,對於成長的訴求都是一致的,都要面對將來要成為一個什麽人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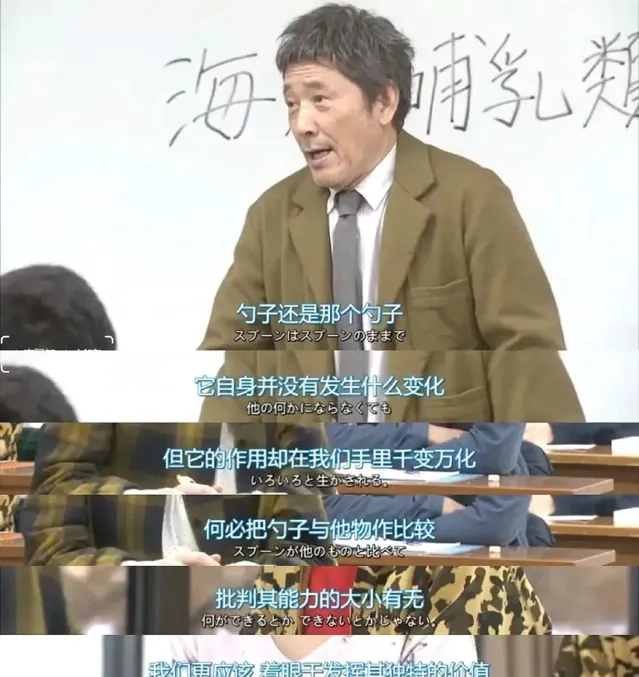
我還發現,漢文本1801班的學生和黃燈老師筆下80後90後,也就是我們那一代人,結構很不一樣。我們的學生大多數人至少是生活在鎮上,而不是像我上大學時的班級,大部份人都來自農村。據我了解,1801班有一半以上學生的父母都是老師或者醫生,這意味著他們有固定的收入來源,也有相對充足的時間陪伴子女。但另外一個影響是,因為很多父母都處在編制之內,有這種人生體驗,自然也會希望子女能像自己一樣過一種穩定的生活。所以我們很多學生一進來就知道自己要考公、考研、考編,父母的掌控反而限制了他們展開自主的摸索。
我們班上有幾位不愛說話的同學,我從一開始就對他們格外留心。秘若琳是從農學院轉專業來到我們班的。魯東大學規定,只有班級前10%的同學才可以轉專業,按理說她應該是專註力很強的孩子,但她剛來時非常安靜,甚至有些自閉。他們大三開學的時候,秘若琳因為胃病突然瘦到了70斤,以至於我走到教室裏都沒認出她來,以為是來班上旁聽的同學。那時她的媽媽就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房子給她做飯,也是在這段時間我對秘若琳了解了很多。從她媽媽口中,我得知她從中學開始就特別喜歡文科,但是因為父母覺得文科沒什麽前途,所以讓她選擇了理科,來到了魯東大學農學院。入學前秘若琳就已經知道了魯東大學轉專業的規定。於是她來到農學院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勁地學習,徹底地離開農學院,離開理科。
班上一位叫楊 聿 艷的同學也是這樣,一開學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我們班最後一個到的,當時已經在開新生見面會了,她急匆匆地跑了過來,坐在墻角。我記得很清楚,她當時的面部神經都是非常緊繃的狀態,兩只手交叉在一塊,使勁地捏著自己。後來她告訴我,當時其實非常緊張,因為上學的時候特別害怕老師,很擔心我會過來罵她一頓。她沒想到我走過來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吃飯沒有,因為當時已經晚上七點多了。

應試教育下,雖然老師也痛苦,家長也痛苦,但是這種痛苦最終都是需要讓孩子去忍受的。 每個個體所能承受的壓力也不一樣,有的孩子耐受力強,或者家人給了他更多的安全感,但有的就不是了。不同的省份的情況也不一樣。我最近和幾個福建同學聊天,才知道他們不少人讀高中時都能談一到兩次戀愛,因為有親戚朋友在國外,出國留學也是很自然的選擇,但這些情況在山東是很難想象的。
1801班有42位同學,來自全國14個省、自治區,其中有28位元同學都來自山東。根據我以往的觀察,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絕大多數人都會去考研、考公或是考編,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同學最終都會成為語文老師。在山東,我們經常開一個玩笑,當爺爺奶奶來看望剛會說話的孩子時,會問他們將來想當什麽。孩子可能會說我想當太空人或者科學家,但馬上就會被爺爺糾正說,要當公務員。在山東人的心目中,老師是歸教育局管的,也屬於一種幹部。
不管是在1801班開展活動,還是發起石榴花讀書堂社團,辦【石榴花】雜誌,最根本的是,我們一直想要對抗應試教育給孩子們造成的傷害。自石榴花創辦以來,我和同事姜娜老師一共舉辦了42期跨學科講座。 透過這些講座,我們想要讓這些孩子和更多的人相遇,建立一種看待世界的多元視角,能夠理解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選擇,更加寬容別人的選擇,最終堅定自己的選擇,而不是被世俗的標簽所框定,能向著別人告訴我的那個方向走。 秘若琳後來考取了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生,當然,這是她自己真心想學的方向。

當時為了幫他們走出這種陰霾,我在每次班會後都會安排一個小的演講環節。表面上是大家自發地上台,但我其實會安排班上這幾個比較內向的同學提前做一些準備。在這種鍛煉下, 楊 聿 艷 後來徹底放飛自我了,參加了學校各種各樣的演講比賽,甚至還取得了好幾次獎項。後來有一次開班會,到了演講環節,我沒有提前跟 楊 聿 艷 溝通,但她主動站上了講台。要畢業離開學校時, 楊 聿 艷 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她已經變得非常自信了,很真誠地和我說,黃老師,如果別人問我你在大學裏學到了什麽,我可以說在教材和小說之外,我還是認真地讀了一些別人沒有讀過的書,寫了很多的文章的。
從大學講台到鄉鎮小學
因為是師範專業,我們的學生都會去到山東的各個中小學實習。作為他們的班主任,我也要不斷地到各個地方調研,看學生們在各個鄉鎮中學的狀態。2021年6月,我坐著高鐵來到臨沂北站,租了一輛車,用6天時間穿越沂蒙山區,調研了臨沂6個縣的鄉鎮中學。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有一個困惑,我們大學裏所謂的貧困生似乎沒有那麽困難。我2004年上大學的時候,貧困是真貧困,班上有同學為了節衣縮食一天只吃一頓飯。但現在大學裏的一部份「貧困生」也用得上名牌手機和膝上型電腦。在臨沂的調研解開了我的這個困惑。
當時我們文學院有一位叫做徐蔓的畢業生在當地做老師。他跟我說,老師你知道嗎,我們班五十多個學生只有兩個是學習的。我最開始感到難以置信,但後來在跟各位校長、教師的訪談中發現,為了孩子能夠上好的初中,經濟條件不錯的家庭早就到縣城到市區去買房了。留在鄉鎮初中的孩子多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隔代教養長大。很多孩子要不父母離異,要不父母癱瘓在床、患精神疾病,再就是父母自殺。徐蔓跟我說,「老師你看,在這樣一個家庭當中長大的孩子,內心缺少安全感和專註力,怎麽可能指望他們能夠好好學習?」優秀的老師也早就跑到縣城和市區去了。大多數初中的孩子到了初二就不斷地跟老師說,我是不會學習的,初中一畢業我就完成義務教育了,就可以到城裏去打工,到餐館裏去端盤子了。 這就意味著真正貧困的孩子和家庭是過不了中考這關的。

當時我的想法就發生了變化。 通常情況下,培養一個優秀的研究生只需要做好我的本職工作就行了。但我想與其這樣,還不如培養更多優秀的語文老師。 當然班上的同學們都希望能夠留在市區當老師,但是還有相當一部份同學暫時沒有考上縣城或者市區的老師。而且根據政策,很多新入職的老師也必須在鄉鎮初中要幹兩到三年。所以石榴花社團所做的事情就慢慢變成一個迴圈:如果能把大學生培養成一個優秀的語文老師,孩子們受的傷害就會更少,就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大學生,再變成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中小學語文教師。
但我始終也知道,教育本身並非萬能的。那次我在臨沂見到徐蔓的時候,我也問過他,是否把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傳遞給這些鄉鎮初中的學生們。他跟我說,他所能做的就是對得起自己,把知道的東西力所能及地傳播出去。那一年徐蔓剛在臨沂工作不久,陪我吃完飯後還要去醫院照顧生病的母親。看到曾經有著飽滿理想的學生在生活中掙紮,我其實非常心疼。臨走前,徐蔓堅持要把我送到最後一個路口。他在路上問我,老師您在高校裏面教書,也會有感到生活很沈重的時候嗎?我當時告訴他,能把讀書、寫書和教書做好,我就已經很滿足了。他說,老師我真羨慕你這種狀態。接下來是一陣沈默,然後我就到路口下車了。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做得比其他人好。說句比較直接的,我能做這些事情是因為已經透過沒日沒夜的努力,把職稱問題解決了。如果我現在還是一個講師的話,我還是會很願意去陪伴同學們,但可能沒現在這麽多的時間去做這些事情。所以我很理解很多老師不是不願意去做,更多是因為他們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
我在高中讀到劉慈欣的【鄉村教師】。裏面講到,以外星人的視角來去看人類的話,不同代的人類似乎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和認知,但他們體內並沒有什麽基因或者細胞來遺傳這些記憶。 後來這些外星人驚訝地發現,人類中存在一個叫做「教師」的群體,正是這樣一群人讓那些精神得以存續。 當時我讀完後淚流滿面,我本來就是鄉村教師教大的。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排版: 樹樹 / 稽核:楊逸
招聘|實習生、撰稿人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
本文為原創內容,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未經授權,嚴禁復制、轉載、篡改或再釋出。
大家都在看
「 點贊 」「 在看 」,讓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