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許誌強
維多利亞時期,在急劇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行程影響之下,英國大量底層兒童得不到有效監管,少年犯罪問題日趨嚴峻,引起普遍的社會憂慮。當時的知名記者詹姆士·格林伍德(James Greenwood)認為,英格蘭和威爾斯每年至少有10萬名16歲以下的少年犯被關進監獄。1847年,議會的下院議員在報告中指出,過去9年中英國12-17歲的少年犯平均每年都要增加近7000人。當時少年犯罪的形勢由此可見一斑。
一、墮入「賊窟」的少年
維多利亞時代的少年犯絕大多數來自底層貧困群體,如學徒、仆人、流浪兒、乞討兒等。他們大多因受了成人的教唆和不良影響而墮入犯罪,借用狄更斯【孤雛淚】中的相關描述來說,他們都是因為種種緣由而誤入「賊窟」的「費根的孩童」。
英國犯罪史學家彼得·金教授(Peter King)指出,這些來自底層社會、未受過教育的青少年在外出學徒至結婚之前往往處在一段「危險年齡期」(slippery age),監管的缺失、生活的拮據和物質的誘惑很容易使之沾染偷盜、賭博、詐騙等惡習。曼徹斯特的警察總長威利斯(Captain Willis)曾在【晨報紀事】雜誌上撰文寫道:「曼徹斯特有一大批非專業的少年犯罪群體,他們在工作之余從事盜竊。許多少年將盜竊作為正式工作之外的一種副業,他們從工廠偷盜棉花以及其他生產資料。」

▲ 19世紀英國竊賊使用的作案工具
從經濟報酬來看,偷竊對底層少年兒童來說也極具誘惑力。根據知名社會改良家查德威克的調查,普通工人辛苦1天的平均收入也不過為3先令,而扒手所得可能是其2倍。盜竊在當時的英國會被視為一種謀生的職業,雖不光彩,但入行者卻不在少數,乃至倫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都出現了專門培訓偷竊技藝的學校,吸引了大量無知的底層少年。
二、善於偽裝的「時髦扒手」
當時,英國的少年竊賊群體也存在著明顯的階層區分。盜竊高手和技藝平庸者之間差異非常明顯,他們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飲食穿戴,活躍於不同的空間場所,甚至享受不同的娛樂消遣。地位低的日常所得甚少,只能聚集在樹蔭下、墻角邊,用骰子和紙牌玩賭博遊戲,每次出手不過半便士。而地位高的所謂「時髦扒手」(swell-mob)的年輕人,他們則多癡迷於玩賽馬和套環,並經常在現場見機行竊。
這些「時髦扒手」,年齡在14-20歲之間,打扮時尚,著裝體面,以此裝扮來迷惑眾人,掩藏自己的竊賊身份。他們是犯罪少年群體中的「上流人物」,具有一定威望和號召力。作案需要人手時,他們會到附近的廉價旅館中尋找幫手,其他男孩都以其為馬首是瞻。狄更斯【孤雛淚】中的「機靈鬼」傑克·道金斯便是一名典型的「時髦扒手」。倫敦有一位叫尼爾森(Nelson)的竊賊,曾是「時髦扒手」中的佼佼者。他經常在商店裏仔細觀察紳士們放置錢包的位置,然後向早已在街道上準備就緒的手下施以暗號,他們相互配合直至順利完成盜竊。他曾自詡已在倫敦操業10年,幾乎沒有失手。

▲ 19世紀末所繪「時髦扒手」的形象
約翰·默裏(John Murrary)曾對這一群體作如下描述:
「那些街角的年輕人,穿著倫敦最時髦的服裝,戴著精致的珠寶,叼著雪茄在那裏吞雲吐霧,有誰能想到,他們竟是衣著光鮮的竊賊、扒手!他們正忙著互換卡片——這倒不假,但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卡片上卻印著昨日所盜贓物的資訊。或許你說不可能,他們那麽年輕,衣著那麽得體,看上去如紳士一般,如何能叫人覺察他們是在做虛偽的勾當呢?」
實際上,「時髦扒手」鮮亮的著裝正是他們掩飾犯罪的重要道具,他們善於以「小紳士」的樣貌讓人放松戒備。他們經常用的作案策略是,在公共場合進行擁擠和喧嚷,故意制造慌亂,並趁機行竊。當時大都市無處不在的群眾性娛樂也為他們提供了作案機會,劇院、體育場、拳擊擂台和跑馬場等都是這些「時髦扒手」經常光顧的場所。
三、無知無畏的硬漢形象
英國兒童犯罪史學者希瑟·肖(Heather Shore)從性別視角對19世紀英國男性少年犯的精神氣質做了分析,她認為從諸多材料描述中可以看出,少年犯群體具有大膽無畏、自恃逞強、渴望成熟等氣質特點。這些特征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傳統「血腥法典」的嚴酷刑罰和後來福音教派的寬仁教化都無濟於事,不能有效抑制少年犯罪問題,因為很多少年沾染了各種社會惡習,早已變得冥頑不化、藐視死亡,這背後體現出了對生命、法律和權威的冷漠和無視。
恃能逞強、無視法紀是維多利亞犯罪少年的普遍特征。少年犯的這種特征與其長期浸染於底層成人世界不無關系。監獄中的少年犯接受體罰或行刑時,其他獄友往往不允許其喊疼、哭叫,甚至不得有任何表情,否則會遭到嘲笑。同夥會說出這樣一些激勵話語:「夥計,要敢於赴死」,「不要丟人現眼」,「要有點男人樣」。在一起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幾位少年犯在獲知自己被判流放刑罰時依然在法庭上表現輕浮,法官提醒他們,流放並非意味著去一個相對閑散的地方,而是持續嚴格地被限制自由,旁聽席上的同夥則對法官報以傲慢的歡呼與尖叫。記者梅修在采訪中也發現,一個窮孩子去偷盜的原因可能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種」,他還發現孩子們經常相互炫耀自己的犯罪記錄,誰進牢房的次數最多便會贏得最多的掌聲。
一名15歲的少年犯向調查委員會描述其團伙的日常行為時說道:「(我們)一天到晚賭博,玩紙牌或擲硬幣,有人喜歡鼓吹炫耀他們曾經的搶劫生涯,有人喜歡詛咒和謾罵,有人喜歡講述艷俗故事,有人喜歡吟唱低俗歌曲。」在底層社會的生存環境中,孩子們所能接觸到的日常娛樂不過是觀看廉價劇場、低俗表演和便士舞會(penny hops),最吸引他們的讀物往往是犯罪故事,耳濡目染,日漸養成種種惡習。許多少年犯將大盜「傑克·謝潑德」(Jack Sheppard)作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此人為18世紀的知名竊賊和越獄高手——曾4次成功從監獄中逃脫。當時流行的犯罪文學、犯罪戲劇透過細致再現各類大盜們的犯罪情節,使兒童觀眾或讀者迷戀其中,這在無形中讓他們熟悉了犯罪的伎倆和方式,有些孩子甚至對知名大盜的傳奇經歷產生了膜拜感。
四、不斷蔓延的社會恐慌
自19世紀40年代開始,英國少年犯罪話題開始迅速進入公共輿論,並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恐慌。產生恐慌的主要原因在於,它是一個非常棘手但又一時無解的社會問題。
維多利亞早期的英國人對其陳舊的刑罰體系早已喪失信心,而有效的少年犯罪監管模式尚未確立。當時的一位監獄管理者指出,許多孩子被關押在成人監獄中,不久便被釋放,如此迴圈,日漸沾染更多成年犯人的惡習,從最初的幾乎稱不上犯罪的行為(乞討),逐漸成長為一名小偷、盜竊犯、大盜,乃至於任何社會舉措都難以將其挽救的惡棍。隨著大量越軌少年逐漸成長為成年人,英國人則不得不面對更加糟糕的社會失序問題。這些底層少年不僅是家庭的棄兒,也是社會的棄兒。他們之中大多無父無母,即便有,父母亦缺乏教養子女的責任心,甚或父母本身行為不檢,以致殃及孩子的成長。當時地方政府嚴苛的濟貧政策以及社會上短時性的慈善救助都難以讓這些失足少年獲得相對穩定的支持,也就難以改觀不斷惡化的少年犯罪形勢。當時少年犯罪的改革家瑪麗·卡朋特認為:「今日少年犯罪的嚴重性與廣泛性已經成為令整個社會最為痛心和關切的事情。近來經由各類出版物的描述和揭露,他們成熟而固執的本性已在公眾面前展現無遺,幾乎令每一個虔誠之人心驚膽寒。」
針對嚴峻的少年犯罪問題,英國社會上發起了有獎征文活動,以促進對該問題的深入探討。1849年亨利·沃斯利教士(Reverend Henry Worsley)的獲獎著作【少年之墮落】對此種恐慌有這樣的描述:「社會之惡就像身體上的一處潰瘍,不斷蔓延和擴大,散布其破壞性影響……少年犯罪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和潛伏性的違法活動將會致使英國的工業走向蕭條,農業變得萎靡不振,商業逐漸消失……」米卡婭·希爾(Micaiah Hill)則在其【少年犯罪】中呼籲:「當務之急,要發展教育!還是發展教育!否則,英格蘭的旗幟將被摧毀,日落黃昏之後將是血海一片。」可以看出,維多利亞早期英國社會對少年犯罪的恐慌不僅僅局限於犯罪本身,而是犯罪亂象對社會道德的沖擊,對宗教信仰的褻瀆,對民族力量的削弱以及對法律權威的藐視,它會侵蝕和瓦解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和秩序體系,減損英格蘭的文明特質和工業積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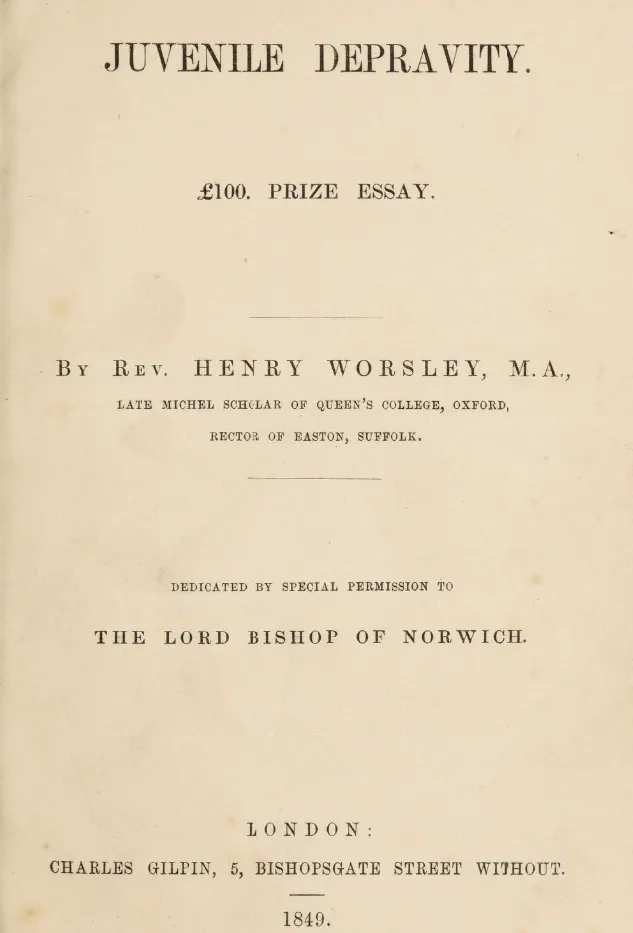
▲ 沃斯利獲獎著作的扉頁
針對少年犯罪問題,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對於政府責任、家庭角色、社會立法、刑罰制度、貧困救濟、兒童福利、教管制度、教育改革等諸多方面展開了深入而持久的討論,也促發了一波又一波社會變革。到19世紀中後期,英國逐步建立起分類監管、規範嚴格的少年教管體系,不僅有效地抑制了少年犯罪問題,也促使大量失足少年重新回歸社會。
(參考文獻從略,詳見原文連結。 作者新著【近代英國的社會犯罪治理】由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23年出版。本文部份內容見於是書第一章,寫作本文時對文字有一定調整和改動。)

本文先發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歡迎點選下載「澎湃新聞」app訂閱。點選左下方「閱讀原文」即可存取全文。
投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