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初聽二手玫瑰,是被他們的歌詞打動的。 梁龍在【樂隊的夏天第三季】裏曾說:「二手玫瑰的歌詞是有一定文學性的。」 二手玫瑰解除安裝了上一代搖滾人背負的文化包袱,不再借助針砭時弊的吶喊和嘶吼,而是換以幽默的、調侃的、反諷的、帶有民間曲藝性質的歌詞和串詞,呈現他們嬉笑怒罵的娛樂面貌。一個搖滾樂隊該做的不該做的、出格的別具一格的、不可理喻的出其不意的界限就此變得模糊了,仿佛他們在舞台上怎麽都行,沒有什麽光怪陸離會出人意料,他們說什麽、幹什麽都更容易被認可,任何經由他們使用過、調教過的或高雅或庸俗的「二手」語句,無論是對性的明示還是對社會問題的暗示,總能平穩遊走於可被容忍的邊際以內。
可以說,歌詞、串詞及各類言論共同構成了二手玫瑰最搖滾的部份,若非如此,他們的魅力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頻繁上綜藝、錄短視訊、當美妝博主,極盡跨界和顛覆之能事,制造話題的能力甚至超過音樂創作的激情,梁龍和二手玫瑰讓不少歌迷有點摸不著頭腦—— 「看來你是學會新的賣弄了,要不怎麽那麽招人的喜歡,可是你還是成了一個啞巴,神神叨叨地說著一些廢話」(【伎倆】) 這到底是在諷刺誰呢?在梁龍看來,這些都是為了讓搖滾樂在大眾眼前再燃一次,只想「稍微能讓大家忘記我的速度慢一點」。可這究竟是想讓美妝界、剁手黨還是歌迷們多記住他一會呢?顯然,他都想要,但也知道各界之間少有交集,跨界只是一種交流,不敢奢望歌迷之外的他者認同,但亦不肯放棄多渠道銷售巡演門票的大好機會,由此便走上了一條帶貨搖滾和搖滾帶貨的新路,在直播間一邊賣化妝品一邊推銷自己的樂隊和音樂。 當商業產物內建多棱鏡,對映出包含文化、商機、個性、零規則等多重涵義時,梁龍當然不會錯過秒速破圈時代的到來 ,但如何解決眾媒環境下的傳播困境,成為擺在他面前的首要問題,最佳選擇無疑是在自媒體化浪潮中隨波逐流,即以人格化特征打造獨特的內容輸出平台,進而完成對粉絲的拉新、留存、促活、轉化等消費閉環。 對梁龍來說,墨守陳規地去做所謂的藝術品似已失去意義,在商業模式上的持續實驗和創新,要比將同等乃至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單純為藝術做同樣的努力上,更能迎合娛樂至死的神經,也就更具博取持久成功的價效比。

其實梁龍也很清楚,直播也好,短視訊也罷,終究不是長久之計,破圈於他不過是為了找到另一條謀生之路,這並不是說在搖滾界連梁龍都找不到生路,而是以此換得在搖滾以外快速擴張所需的各種支持,盡管搖滾依舊是那個不變的前提,但是單純創造搖滾樂是有局限性的,因為被感動的永遠都是同一小撮人,如果想讓更多的人知道和接納搖滾,就要將其變成更廣泛的藝術。 而這有賴於在當代文化和藝術市場裏找到一條線索或者一個平台,用更復合的方式證明音樂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並存感,將搖滾樂像其他藝術門類那樣做成值得收藏的藝術品,並讓其中的優秀代表透過公共手段進入大眾領域。 「看那藝術像個天生的啞巴,它必須想出別的辦法說話」(【伎倆】)。 按照幕後策劃人的觀點,進入中國搖滾史很簡單,一個樂隊只要能存活五到八年,無論活躍與否,基本就算在中國搖滾史中留名了,但二手玫瑰的目標應當是努力進入中國文化史的殿堂。吊詭的是,在為搖滾設計的宏偉藍圖中,搖滾的存在感卻不及其他藝術領域的友軍,多少顯得有點底氣不足。
作為草根樂隊的代表,二手玫瑰的成功翻盤,不僅給逆天改命的神話加上了最好的註腳,也使梁龍在商業上的「通透」獲得了市場和資本的正向評價,前者高度契合普通歌迷渴望自己也能闖出類似成就的希冀,後者透過梁龍對商業是藝術假想敵的批判試圖進一步維護和鞏固「通透」的正面形象,因為這與中國早期很多搖滾樂霸主的理念南轅北轍,那些至今仍在搖滾界舉足輕重的大佬們至少曾經認為,音樂不能商業化,商業就是妥協,就不搖滾了。張楚當年走紅後,有品牌商邀請他出席活動,一場幾萬元,他十分拒絕,原因是:「選擇搖滾樂並不是為了成為娛樂明星,而是內心的一種撫慰。」有奢侈品商找崔健代言,經紀人幫他談好了五百萬的價格,他卻撂下一句:「我們這樣搞,和那些明星有什麽區別?」 梁龍卻認為,將商業與藝術對立起來,是虛設和扭曲了藝術的假想敵,他也承認存在某些妥協過分的情況讓人難以接受,但不應一上來就把商業當作自己的敵人,如果把假想敵弄錯了,基本上就喪失了藝術創作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崔健、張楚們的搖滾時代之所以轉瞬即逝,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不「通透」使其被時代拋棄了,自由奔放的歲月過去了,社會極速進入商品經濟時代,商業占據主流,人們內心追求的,是一個金錢的社會,而不是藝術的社會,不管是搖滾教父還是魔巖三傑,在此背景和洪流下,都不過是一群不合時宜的凡人。
不得不承認,這種觀點坦率而真實,唯一的缺憾在於,未經抗爭就繳械的方式很不搖滾。至於那群不為商業化折腰的搖滾人,很難說是時代拋棄了他們,還是他們拋棄了時代。

張楚曾經說過:「在那個時候,你已經成為一個新的你,而別人還沒有成為一個新的我,那種孤獨的滋味,是很不舒服的。」 體驗過這種孤獨並沈浸其中尋找新的力量和出口的人,相較千方百計抗拒和逃離這種感覺和狀態的人,總有一份內心的篤定,是任由外部世界如何變化或外力作用怎樣影響,都不能撼動的。自始至終都能擁有這份篤定的人是幸運的,經歷過抗拒和逃離後回歸這份篤定的人則是圓滿的。遺憾的是,梁龍暫時還未做好與後者結緣的準備,而是嘗試將自己在商業和藝術關系上的「通透」解釋為某種程度的「被迫」和「無奈」,盡量避免不同理念之間不必要的沖突對其人設和品牌的負面影響。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賣賣……我往哪逃?」(【火車快開】) 直接挑明在時代浪潮面前選擇縱身一躍實屬逼不得已,緊接著又丟擲靈魂拷問 「我看你往哪逃?」(同上) ,不僅對嘲諷他的人予以反唇相譏,也在暗示其實大家都一樣的同化心理。在所有人都不可避免要下水的節奏裏,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商人」(【允許部份藝術家先富起來】) 就不僅顯得苦澀因而值得同情,而且能使所有主動或被迫落水之人在哀己憐人的情緒裹挾下,與之產生 「我被活活的逼成了個廢人吶」(同上) 的共情。
商業模式、宏偉藍圖和「通透」人設全部湊齊後,二手玫瑰距離搖滾獨立、自由的精神內核卻越來越遠了。商業的加持必然會導致獨立精神的部份喪失,但這遠非唯一損害二手玫瑰獨立精神的因素。 面對「大哥你玩搖滾,玩它有啥用啊?」這種典型的目的論質疑,盡管後來梁龍運用自嘲的方式將其轉化為樂隊的標誌性slogan之一,但這種刺激對他的負向影響卻不絕如縷。 關於目的論,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有些事物是自然存在的,有些事物是由於別的原因而存在的,自然存在的事物會遵守內在的執行法則,由於別的原因而存在的事物是按照事物之間的關系被安排就位的(【物理學】)。當搖滾人「依照自然」的執行法則進行創作,嘗試成為一種自然的存在,結果無人問津時,很容易聯想到,搖滾是否可以成為由於別的原因而存在的事物呢?
既然現實中的存在已不再是被自然的內在原則——即獨立、自由的搖滾精神——定義價值的,那麽,即使運用「不自然」的方式,也不會對其構成具有譴責意味的拘束。於是,二手玫瑰將他們的搖滾嫁接於二人轉之上,使搖滾變成由於二人轉而存在的混搭音樂。 可實際上,梁龍起初是看不上二人轉這種在他眼裏象征著貧窮、落後和跌份兒的民間音樂形式的,「農村那玩意兒,我們城裏人不懂。」 直到離開東北,他都沒怎麽聽過二人轉,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玩意兒」,只能算是他的零碎記憶。可見對於梁龍而言,二人轉與搖滾一樣,也不是「依照自然」的那個存在,甚至連音樂本身都可以被弱化為由於服飾、美妝、舞美、裝置、繪畫、MV以及與藝術家合作的Video等元素構成的有機整體而存在的一個分支,並且同樣不能由此推出這個有機整體就是自然的存在,所有可能涉及的藝術領域都是由於名利的原因而存在的,當然也就可能出於同樣的理由而隨時被邊緣化抑或被舍棄,唯有名利才是那個不變的終極目的。

當此終極目的得到滿足前,受其支配的人出於對名利的一腔熱誠,無論希望多麽渺茫,即便忍受再多的艱辛和苦痛甚或放棄再大的利益和誘惑也能甘之如飴,這是一種在成名後會被奉為美德但在生活中經常不被理解的奇怪體驗,幾乎能在每個成功者和每部成功學中覓得,並在星火相傳之中被人為昇華和神化至本不配享的程度和高度。 職高畢業後,梁龍在齊齊哈爾某化妝品公司當銷售主管,可他始終放不下搖滾的念頭,幾經猶豫,最終還是決定辭職進京去找機會。 「究竟是什麽,讓我無法自拔?」(【征婚啟示】) 也許是向往黑豹、唐朝這些搖滾巨子們可以在五星級酒店連住一個月的生活吧,這種名利雙收的成就感是區區銷售主管永遠體驗不到的。縱使 「混到了北京,我混沒了牽掛,混亂了生活,我混長了頭發」(同上) ,仍舊不肯放棄一定要出人頭地的執念, 「如果你恨,你就恨出個追求」(同上)。
一旦對名利的渴求得到滿足後,感覺就像某一天在十字路口突然暈倒,整個世界在自己面前一下子就崩塌了,不知道該幹什麽。 「只是理想咋突然那麽沒勁,看著你我也再說不出什麽詞兒」(【伎倆】);「從前的理想看來挺可怕的,愛情能當飯吃會更偉大,為了能有個新鮮的明天,你再也聽不懂你說的是啥。」(【采花】) 功成名就的快感遠不如做白日夢時來得多,名利的意義在於被不斷追逐而不是真被實作,或者說是永遠實作不完的,那種一勞永逸的幻想是徒勞的,很快便會有下一個目標等待所有人競相實作,如果不能繼續成為那個幸運兒,就會被永不停息的娛樂精神拋棄, 「我努力地攻擊著花的蕊呀蕊呀,玫瑰呢呢喃喃說位置不對不對呀」(【好花紅】),「我必須學會新的賣弄呀,這樣你才能繼續地喜歡吶」(【伎倆】) ,周而復始,直至被名利吃幹榨凈,對資本、市場和觀眾失去利用價值,然後仍會被毫不猶豫地拋棄,正如當初為了追名逐利可以舍棄搖滾、音樂、生活和幸福那樣,因為其與所有被舍棄的並無二致,都是由於名利的原因而存在的,而非自然存在的,或者說不是獨立存在的, 因而不可能擁有獨立價值和獨立精神,也就無從獨立判斷這個時代還需不需要批判?什麽樣的批判才是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批判者對世界的認知就一定具有前瞻性和借鑒性嗎? 而且無法獨立思考仍在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既然想不明白,那就幹脆認定這些與自己不存在利害關系,隨後回過頭去繼續講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熟悉的故事,當這些有限的內容被自己講完或被時代改變,沒有故事可講的時候,方才急於從自我經歷的記錄者和講述者向大眾生活的觀察者和思考者轉型,但又受限於獨立精神的慣性缺失,往往漸趨失語。
如今,人到中年的梁龍更願意追憶青春,回想那些他還把搖滾當作個人理想和使命去表達的歲月。他也很想看到一些還在堅持聽現場的70後,若有所思地閱讀二手玫瑰的歌詞,就像當年那些歌詞好像對他們有些打動。 他曾評價九連真人:「他們像我們70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時做夢的狀態,他們那種對音樂的沖動,那種在舞台上不算歇斯底裏但有點抽動的狀態,挺不當代的,很過去時,但特別珍貴。」 假使他的商業模式和「通透」人設真能幫他實作宏偉藍圖,恐怕未必會將內心深處的隱秘角落讓給過往的榮光,而不是睥睨一個親手開啟的新時代。在這懷舊的剎那,讓人頗能體味幾分欲拾朝花而不得的感傷,尤其是當他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曾經的沖動,既未遠離自己,也從未遠離搖滾的時候。但若僅憑這份惆悵就預言二手玫瑰終將回歸搖滾初心,則是未曾覺察他們根本沒有這種自由的想當然。 「你已不是個窮光蛋,這裏不再是你為所欲為的樂園,這裏不再有屬於你的危險,這裏不再是你刺激的樂園。」(【招安】)

很難想象,與搖滾精神背道而馳的不自由竟與號稱「搖滾教母」的梁龍始終如影隨形:早在初遇搖滾之時,梁龍一定不曾料想,有朝一日自己的音樂風格竟然會是現在的模樣 ,換言之,二手玫瑰應該是什麽樣的,並非按照梁龍對搖滾的初心從一開始就明確下來的,而是在目的論的指引下極不自由地幾經變換的;在解釋樂隊名稱「二手玫瑰」的含義時,出於對成名前的某種事後考慮,在不同時期給出的版本也不盡相同,歌迷們需自行辨別何種表達才是自由真實的。凡此不自由者均源於精神不獨立,而精神不獨立又是目的論導向的必然結果,所以理論上,只需減少對目的論的興趣即可避免被帶進死胡同的危險。然而,目的論很容易示人以極大程度的樂觀主義傾向,即宇宙和世間萬事萬物,都在朝著比之前更好的方向發展。這固然是激動人心的,特別是當剛剛步入商業社會或者處於商業社會快速發展時期,所見所聞無不印證此種論調理應成為公共理想。可惜這不是事實,但凡審視一番歷史長河,就不難發現曾經有過很多類似的階段,都如白駒過隙般煙消雲散了。 可是,理想一經樹立,不僅難以連同既得利益被主動放棄,更不見容於來自外部的動搖企圖,大概只有時間才有資格宣布結局,繼而安撫無數受傷的心靈吧。 彼時,目送公共理想時代結束的人們,始得以獨立和自由的精神,迎接個人理想時代的到來。
事實上,越來越多新生代搖滾樂隊,在自己的小圈子裏,做著自己喜歡的音樂,沒有商業模式創新的輔助,也不去思索未來將在搖滾史上留下是否濃墨重彩的一筆,自顧率性而為,自由發展,線上上線下打動並積累了一批認同其搖滾理念的樂迷,怡然躬行著搖滾人渴望達到或者期盼回歸的自然狀態。不知能否在他們中間聽到那熟悉的曲調: 「心若走遠眼若不見是否就看到明天?」(【串門】)
點選訂閱⬇️⬇️⬇️
【愛樂】2024年第5期
「AI與音樂創作的未來」
本 期 精 彩
主題|AI與音樂創作的未來
華彩|藝術家的窮途末路?
更 多 精 彩
前奏|自由的鳥鳴,抑或音樂的樊籠?
幕間|在嬌美的五月
回旋|人生即賦格
行板|琉森:古典音樂狂熱
專欄| 袁樂—老搖滾的絕唱
鷺鳴—伍爾夫的音樂典故
安可|讓老歌換新家
點選下方圖片⬇️⬇️⬇️
獲取【愛樂】數位刊全部精彩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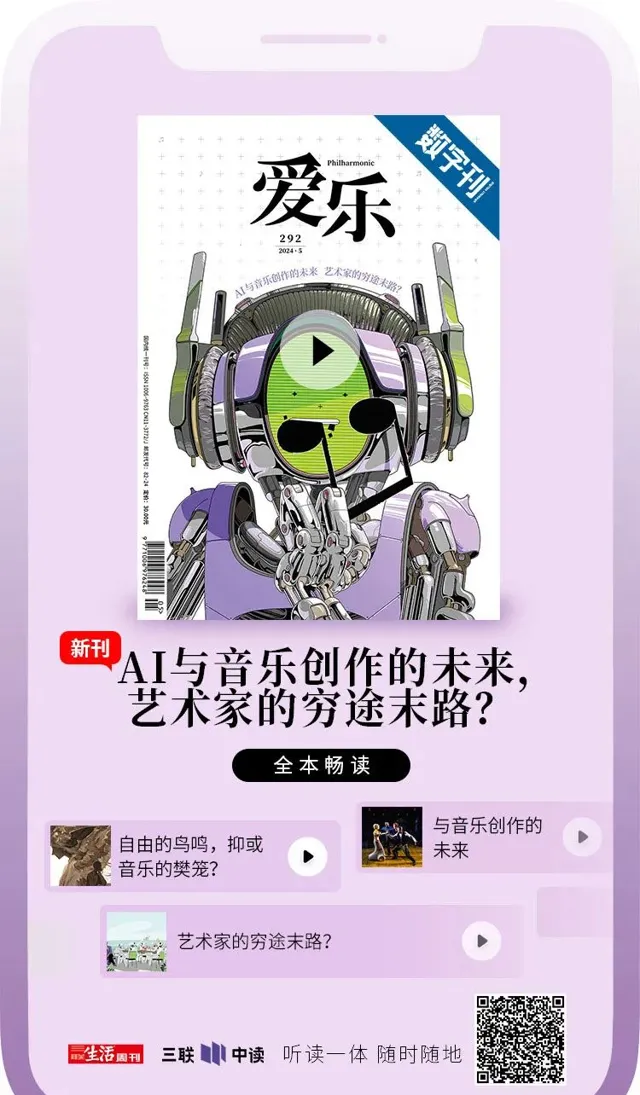
點選訂閱⬇️⬇️⬇️
【愛樂】2024全年紙刊












